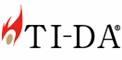
2009年10月12日 16:57
首先要替唯色澄清的,她作為達賴喇嘛的「不知疲倦的孩子們」之一,她一直選擇的是「中間道路」,以中國各民族的和解與和諧為念,要求身為中國公民的權利。
目前的中國境內所發生的事情,2008年三月以來對於藏地的鎮壓,新疆的種族仇恨與對立演變成盧安達程級,背後的深層理由與心態,對於身在台灣的我們來說並不陌生,比方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那種對外人懷疑歧視的心態;或者是「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對於統一即代表富國強兵,國力強大--那種未經過實驗即成真理的迷信;或者,對於中國把從來沒有治理過一天的台灣,視為自己的禁臠,動輒稱之為「我國台灣」之霸道野蠻,我們都有切身的體驗。也難怪我輩台灣人皆對「大一統」這個名詞感到戒慎恐懼。
然而,假如大一統不是像中國那樣的搞法呢?有沒有可能不但不是玉石俱焚,失去了自己國家的自治與主體性,並且還繁榮發展,更上層樓?這個遼闊的世界當然有這樣的例子,那就是蘇格蘭與英格蘭。
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以蘇格蘭的歷史為例,檢視小國面對大國時,如何在獨立或統一的過程之中,保持主體性。第一部份描述蘇格蘭建國的史詩,看蘇格蘭的先人如何為保有自由而不懈地努力;第二部份,則檢視蘇格蘭與英格蘭共組大不列顛的共榮與成就,旨在反駁中國目前民族政策思考上,「自治必定會造成分離」之謬論,另有中國學者所認為「民族區域自治」之前例只限於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蘇格蘭的例子足以證實其立論之偏狹。我欲申論以民族自治為基礎的大一統,事實上真有可能雙贏。
然而必須強調的也是,我亦是在蘇格蘭的例子中,看到民族主體、國家主體性的重要,並主張不管台灣未來如何,我們現在必得為我們的獨立與自由繼續奮鬥下去。
在蘇格蘭建國的過程裏,可以見到弱小國家企求建立自己的身份與認同的過程。其中的堅苦卓絕,含莘茹苦,比起台灣近幾年爭取獨立的奮鬥,圖伯特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為建立獨立國家的努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歷史的開頭,蘇格蘭與英格蘭就有不同的發展。公元43年,羅馬帝國大軍成功入侵英格蘭,並且平定了東部布狄卡(Boudicca)女王的叛亂後,北方的「加勒多尼亞」(Caledonia)還是保持自由。此地區的人,除了低地所居的皮克特人以外,就是來自愛爾蘭島、說著蓋爾語的蓋爾人(Gaels)也在西邊的群島上建立起自己王國。公元84年,羅馬軍隊決定繼續北征,遇到北方部族的激烈抵抗,在西北部的高原打了非常慘烈的一役,羅馬軍隊雖然獲勝,然而最後因 羅馬帝國內部的動亂,未能殖民此地;羅馬皇帝並於122年興建「哈留良長城」(Hadrian's Wall),直到公元430年羅馬軍隊撤離為止,城牆以北都被定義為「野蠻」之地,相對於羅馬帝國的「文明」。然而,蘇格蘭也發展了自己的文明,在公元536年,基督教的信仰由聖哥倫巴(St. Columba)從愛爾蘭帶來,並廣為傳播。
中世紀蘇格蘭第一個王國,就如同許多國家的建立一樣,是由外敵所逼迫。公元635年,英格蘭中部的盎格魯王國北侵,皮克特部族聯合起來,誘敵深入高地加以殲滅,稍後建立起皮克特王國(the Kingdom of Picts)。公元834年,來自海外的維京人搶劫虜掠不列顛大島,肯尼斯‧馬克亞平(Kenneth McAlpine)領導部族擊退維京人變成皮克特王,稍後,他的孫子康斯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除去了篡位者,改國號為阿爾巴王國(the Kingdom of Alba),阿爾巴為蓋爾語(Gaelic)的蘇格蘭之意,蘇格蘭王國於焉誕生,年代為公元900年。
康斯坦丁二世即位首先面對的,就是與南方鄰居英格蘭的戰爭。安格蘭國(Angleland,後來變成England)的國王、日耳曼裔的國王愛瑟斯坦(Athelstan)決意完成羅馬人未竟的雄心,統一不列顛大島。公元934年,愛瑟斯坦揮軍北上,軍隊圍困了敦那塔城堡(Dunnottar)的蘇格蘭王,康斯坦丁不得不投降,尊愛瑟斯坦為自己的領主。然而康斯坦丁並沒有打算就此臣服,他決定跟維京人聯盟。三年後,公元937年,在英格蘭的布魯那伯一役(Battle of Brunanburh)攻擊安格蘭軍。後者雖然獲勝,但也元氣大傷,對北方領土確定無力管轄,蘇格蘭因此確保了獨立不受南方王國的統治。然而這個模式--英軍北侵、蘇人臣服、反叛、尋求與外國連盟、反擊--的模式,將會再度重覆。
蘇格蘭獨立地位的最大危機,發生在一二九零年代,蘇格蘭王亞歷山大三世於1287年去世。他生前,由於其子嗣早夭,他曾指定決定王位應該由遠嫁挪威國王的女兒所生之孫女來繼承,沒想到這個小女孩卻於1290年死於從挪威渡海前來的旅途之上。蘇格蘭的王位後繼無人,轉變為一大危機,可能引發內戰。
攝政的護國士(the Guardians)於是請亞歷山大的妻舅,有威信又深諳法律的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來決定該由哪一位有遠親關係的貴族來繼任。沒想到,愛德華竟然轉而要求蘇格蘭王位候選人必須先承認他為共主(overlord),否則他不予裁決。諸位蘇格蘭貴族唯恐失去資格,不得不俯首稱臣。於是愛德華不費一兵一卒,成為了蘇格蘭的統治者。
約翰‧貝里歐(John Balliol) 由愛德華選定為蘇格蘭王。然而他一即位沒多久,愛德華就開始插手管蘇格蘭的事情,不僅干涉司法裁判,還要求蘇格蘭派兵加入英軍到法國去打仗,並且增加賦稅。蘇格蘭前此從來沒有被一位英格蘭王直接統治過,深感「是可忍,孰不可忍」,紛紛起來反抗。1295年,蘇格蘭與英格蘭的交戰國法國簽定了聯盟關係(the Auld Alliance )(註1),此舉已經背叛了之前對愛德華效忠的誓言,愛德華立刻派出軍隊攻擊邊界城市、中古時代經濟規模僅次於倫敦的大城伯瑞克(Berwick-upon-Tweed),此城雖然投降,然而愛德華毫無憐憫,屠城兩天,血流成河,男女老幼倖免者寡。
接著,英軍繼續北進,大敗蘇軍於鄧巴(Dunbar),國王貝里歐不得不投降。然而投降對愛德華卻是不夠的,他摘下了貝利歐的王冠,還把他衣服上的王室紋章撕下,徹底予以羞辱,稱他為King Nobody。貝利歐國王,以及其他被俘貴族被送入倫敦塔,稍後遭流放。
做到這種程度還不夠,愛德華的野心是徹底消滅蘇格蘭國家象徵,使之成為自己的領土,就如同他先前消滅威爾斯王室一樣:他取走了加冕蘇格蘭國王的命運之石(the Stone of Destiny)、聖瑪格利特的黑色十字架(the Black Rood of St. Margaret),甚至有加冕蘇格蘭國王特權的法夫子爵(Earl of Fife)也被他劫到英格蘭去。
然而愛德華的征服大夢畢竟事與願違。一年之內,1297年,蘇格蘭各地反叛峰起,北有安竹默瑞(Andrew Murray ),南有威廉華勒斯(William Wallace),開啟了蘇格蘭獨立戰爭的序幕。其中最有名的一役,就是威廉華勒斯所領導的業餘隊伍,只憑著長矛與戰略,在史德靈橋(Battle of the Stirling Bridge)打敗盔甲厚重、訓練有素的專業騎士軍隊。這在中古歐洲是聞所未聞的一件事,驚人的勝利。此役後,華勒斯成為護國公,並率領軍隊深入北英格蘭,侵擾攻擊,卻沒有辦法攻下英格蘭皇室的城堡。
愛德華並未死心,1298年捲土重來。這一次他在福爾科克(the battle of Falkirk)打敗了威廉華勒斯,後者在戰敗後不得不辭去護國士之職。然而許多蘇格蘭人還是繼續反抗英國的統治。接連六年,愛德華每年都北上,整編軍隊,攻城略地,把蘇格蘭南部變為焦土,所過之處,留下長遠的仇恨。比方說蘇格蘭西南部的蓋勒威(Galloway),凱拉文拉克(Caerlaverock)城堡中的三百人,全部被吊死於護城牆外。愛德華還想辦法建造愈來愈大的攻城機器(trebuchet,投石機)來摧毀蘇格蘭的城堡,史特靈城堡一役演變為戲場,雖然此城中人已經投降,愛德華不管,因為他特地為宮廷中的婦女建造觀賞台非得派上用場,城堡還是慘遭大型的攻城機摧毀。
除此之外,愛德華也在外交上設計將蘇格蘭消滅,他於1301年向教廷(等同於中古時代的聯合國)申訴,流放的貝里歐不是什麼蘇格蘭王,因為蘇格蘭已經不存在了。蘇格蘭的主教們立刻採取行動。蘇格蘭的教會不像英格蘭主教完全臣服於英王,他們享有獨立於國王的權力,所以假如蘇格蘭變成英格蘭的一部份,他們將來就必須臣服於英格蘭的大主教了。不想受英格蘭教會的管轄,擁有可以直接向教皇訴願特權的蘇格蘭主教們,立刻派出懂得法律的使節到教廷去向教宗申訴,說蘇格蘭自古為與眾不同的一個民族,並詳述愛德華在蘇格蘭所犯下的暴行,教宗對蘇格蘭相當同情,判決貝里歐還是蘇格蘭王,應該回到蘇格蘭去即位。
然而貝里歐已經灰心喪志,不想再回到蘇格蘭去,寧願留在法國終老,蘇格蘭王雖然未死,然而卻沒有辦法幫助蘇格蘭了。1304年在史特靈城堡被圍的戰役之中,一旁的修道院內,格拉斯哥主教威夏(Bishop Robert Wishart),暗中與有王位繼承資格、時年二十九歲的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1274-1329)協商,假如他願意出來領導反抗,就封他為國王。
另一方面,經過了六年的戰爭,蘇格蘭的貴族覺得筋痺力盡,打算跟愛德華講和,愛德華勝利在即,居然一改作風,寬大為懷起來,答應只要奉他為王,就可以保留原來的土地與特權。蘇格蘭所有的貴族皆降,只有華勒斯與他的追隨著拒絕向愛德華輸誠。1305年,華勒斯被蘇格蘭貴族逮捕,被送到倫敦。在西敏寺,愛德華下令組成的法庭指控他叛國,華勒斯反駁,說他從來未向愛德華宣誓效忠。然而他的罪未審先定,被處以英國中古歷史的最極刑(Hung Drawn Quartered),屍體被切成四大塊,被送到蘇格蘭的四大城鎮示眾。
1306年3月羅伯特‧布魯斯受主教威夏的加冕,即位為王。然而,他的即位也代表竄位,忠心於貝里歐王的康明家族(the Comyns)與他干戈相向,他兩邊受敵,不只要對付英格蘭軍隊,也必須解決康明家族的不服。面對英軍的首役,是同年六月的梅斯文戰役(Methvan),他被愛德華的軍隊連夜偷襲,損失慘重,蘇格蘭的主教們被俘,他的妻子女兒姐妹稍後被捉,落入英人手裏,他往西逃到陸地的盡頭,甚至不得不渡海,躲藏在愛爾蘭海上的小島。
然而他消失的這段時期,也許最神奇的轉變是他再出現時,不再是一個遵守中古世紀交戰規則的騎士,而變成游擊戰、打帶跑的策略家。命運之輪也似乎開始轉向了,他在戰場上(Glen Trool and Loudon Hill. )取得勝利。命運女神的真正微笑,也許是在1307年,長腳愛德華一世、「蘇格蘭人之鎚」(Hammer of the Scots)在前往蘇格蘭的征途上過世,他的兒子愛德華二世宣布停戰兩年。
雖然不必再面臨可怕英格蘭戰爭機器的進逼,布魯斯的建國工作仍然未完成,首先,他必得繼續平定康明家族的反對勢力,取得蘇格蘭貴族的支持,還得消除蘇格蘭境內的英格蘭勢力。其二,他必須讓英格蘭國王、教廷確認蘇格蘭的獨立地位。其三,為了確保蘇格蘭的獨立,必須解決繼承問題,亦即,他必須生下合法的子嗣。
第一點他可以開始進行,本來不支持他的蘇格蘭人,因為他高舉反抗英格蘭的旗幟,又是唯一打敗英軍的力量,開始漸漸投到他的門下。第二點,毫無進展。第三點,根本不可能,因為他的妻子還在英格蘭的修道院裏囚禁著。
在布魯斯的領導下,蘇格蘭軍開始慢慢克復英人所統治的城堡,最後只剩下兩個城堡未攻下,那就是史特靈城堡以及伯瑞克城堡。史特靈城堡的守城者已經到了守不住的邊緣,向英格蘭請求支援。1314年愛德華二世不得不回應支援,他舉軍北上,然而所遭遇的蘇格蘭軍隊不只身經百戰,而且深諳戰略,在巴那克本一役(Bannockburn),英軍慘敗,潰不成軍,愛德華二世僅以身免,僥倖逃出。
這場戰役確立了布魯斯作為蘇格蘭國王的地位,終結了英格蘭的統治野心。更好的是,戰役之人質的交換,也換回來布魯斯的王后、女兒、之前被俘的蘇格蘭主教等等。然而,讓蘇格蘭獨立地位獲外國的承認,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愛德華二世雖然沒辦法克復蘇格蘭,卻開始他的第二戰場,外交戰--直接向教皇陳情。
1318年,蘇格蘭人發現,英格蘭人已經說服了新上任的教宗,說兩國的戰爭,完全是蘇格蘭的錯,教皇於是下令懲罰蘇格蘭,布魯斯、與他的主教被革除教籍,教皇還下令在每一個英格蘭教會裏,每天舉行三次詛咒羅伯特布魯斯的儀式。1320年,蘇格蘭遣使送了一封信到教廷,這就是蘇格蘭史上最有名的文件:阿布羅斯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Arbroath),其中不僅定義蘇格蘭國王與人民的關係,乃是一份契約關係,宣稱蘇格蘭的人民同意了布魯斯為王,然而假如布魯斯背叛了他們,他們一定會把他趕走,另立新王。「因為只要我們有一百個人活著,我們絕對不願意受到英格蘭任何程度的統治。因我們不是為了財富、榮耀、爵位而戰,單單只為了沒有人願意失去,唯有以性命捍衛的自由。」(註2)
教皇讀了這封信,居然被說服,同意暫時不把布魯斯開除教籍,下令英格蘭與蘇格蘭應該展開協商。1321年3月,協商在班伯拉(Bamburgh)舉行,教廷與法國都派人到場觀察。雙方針鋒相對,辯論內容至少有一部份我們聽了也會覺得耳熟能詳:英方表示蘇格蘭自遠古以來一直屬於英王統治。蘇格蘭反唇相譏,說英格蘭的王位乃是在1066年被「雜種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指征服者威廉,英格蘭的威廉一世)所篡奪,正統應該是威塞克斯王室,而只有布魯斯才是該王室目前的傳人。當然辯論毫無結果,沒有人被對方所說服。一個月後,布魯斯收到了教廷的除教籍令,靈魂永不得救贖。接下來的六年裏,教廷的外交戰繼續,只要蘇格蘭一有進展,英格蘭就有辦法加以破壞。唯一的區別是,1324年王后伊莉莎白終於產下一子:大衛(David II of Scotland, 1324-1371),布魯斯所建的王國終於後繼有人。
轉機,終於在1327年1月20日到來,愛德華二世被他的王后與英格蘭貴族聯手罷黜,二星期後,其子愛德華三世即位。這是蘇格蘭的大好機會,此時已經老邁又疾病纏身的布魯斯集中最後的力氣,在八月時率軍包圍英格蘭北部諾森布里亞(Northumbria)的城堡諾蘭(Norham),英格蘭面臨北部領土被蘇格蘭佔領的威脅,不得不與蘇格蘭談判,後者於10月提出條件,要英格蘭永久承認蘇格蘭的獨立地位,而為了表示誠意,愛德華三世的妹妹瓊(Joan)應該與布魯斯的幼子大衛聯姻。
1328年3月17日,雙方終於在愛丁堡荷里路德修院(Holyrood Abbey)定約。蘇格蘭經歷三十二年的堅苦卓絕,忍辱犠牲,終於取得勝利。教廷也同意解除對蘇格蘭國王逐出教會的禁令,並且承認蘇格蘭的獨立。1329年,蘇格蘭王羅伯特一世去世,兒子大衛於同年6月17日即位。這次新王的即位,還是沒有命運之石的加持(英格蘭還是沒有歸還),然而卻得到了教廷的聖油加冕--在基督教的世界裏,教皇的聖油所加冕的國王,若遭推翻,即犯下了大罪(mortal sin)。英格蘭與法國都有自己的聖油油瓶,終於蘇格蘭也得到了自己的一瓶。
然而三年之後,英格蘭軍還是北侵蘇格蘭;此後兩百年,英格蘭的國王--如愛德華四世(1442-1483)、亨利八世(1491-1547)--都有成為併吞蘇格蘭的野心,不是策反蘇格蘭的貴族,不然就是赤裸裸地帶兵侵略施壓。難怪此時期的吟遊詩人瞎子哈利(Blind Harry, 1440-1492)寫下了威廉華勒斯的長篇史詩,希望所有的蘇格蘭人不可以忘記祖先為求得獨立而努力與犧牲。
雖然英格蘭國王如此無所不用其極,蘇格蘭的獨立地位已經確立,難以動搖,一直到1707年的聯合法案為止。而布魯斯辛苦、忍辱建國的這二十二年,可以說是蘇格蘭歷史上的最重要一章。因為沒有獨立的蘇格蘭,蘇格蘭的文化、宗教信仰與法律、社會制度,極可能會面臨與威爾斯等其他凱爾特民族一樣的命運,那就是被英格蘭所宰制同化,數百年後的現今,仍然必須努力重新建國,以恢復失去的語言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