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01日
《金色的聖山》新書發表會座談紀錄【轉】
懸鉤子:這場座談會是在今年三月在台北舉行的,紀錄九月時整理出來,而我現在才貼出來,因為裏面談的事情是很有趣的,特別是看看一九六三年出生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先生談他自己在康的成長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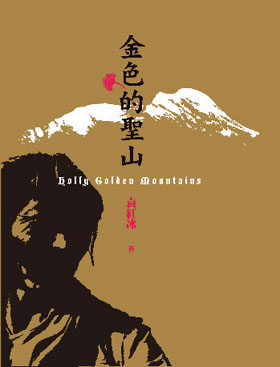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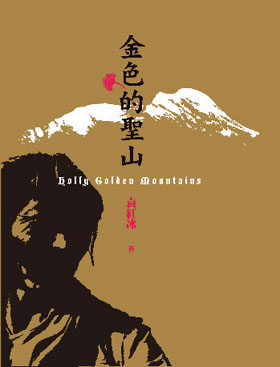
書名:金色的聖山
作者;袁紅冰
出版時地: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
主辦: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2009年3月31日上午10:30~12:00
地點:臺北市臺大校友會館三樓C室
主持: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臺灣圖博之友會監事)
主講:袁紅冰(澳大利亞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首席委員)
與談:周美里(臺灣圖博之友會會長)
跋熱.達瓦才仁(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整理:楊惠羽(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研究生)
校訂:曾建元
曾建元:各位讀友早安,今天是袁紅冰先生《金色的聖山》這本書的允晨版的新書發表會,非常歡迎各位能夠蒞臨今天的會場,首先跟各位介紹今天出席的來賓。我想袁紅冰教授大家都很熟悉了,他為了寫《金色的聖山》這本書,七次出入西藏,我先對他做一點簡單的介紹,最後再來聽他寫作本書的想法。
袁紅冰教授1952年出生於內蒙古自治區,後來在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就學,
與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是同系的前後期同學,一起上過課,但命運不同。袁紅冰本科畢業之後留在北大唸法律學碩士,取得學位之後留下來任教,擔任有關訴訟法方面的課程。在1989年六四之時,他組織了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聲援學生,導致六四之後一度被迫離開教職,在一連串的司法和學術上的迫害之後,最後他被流放到貴州,後來在貴州師範大學擔任法學院長。在貴州期間他完成了他幾本重要小說的手稿,《金色的聖山》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為了讓他的自由創作能順利地問世,袁教授選擇於2004年7月利用到澳洲訪問的機會投奔自由。連同《金色的聖山》在內的幾本重要創作,都是在非常辛苦的、身體與精神皆處於苦難磨鍊的環境當中祕密粹煉完成的。
《金色的聖山》於2005年也曾在臺灣由博大出版社出版過,這次有機會在臺灣的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支持下再版,表示這本書在臺灣和自由世界裡擁有非常多的讀者。我們都非常關心西藏/圖博的問題,特別是對臺灣而言,我們對圖博的民族苦難感同深受,因為雙T(Taiwan, Tibet)臺灣與圖博都受到中國共產黨政權在全世界各處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可以看到袁教授身為一個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如此地關心被中共壓迫的弱勢民族的命運,令我非常佩服。
接下來介紹周美里小姐,她是臺灣圖博之友會會長,她算是圖博的媳婦,他的先生凱度頓珠先生是西藏流亡人民議會的議員。周美里小姐這幾年促進臺灣民間與西藏人民之間的認識,做了非常大的貢獻,如發起成立了臺灣圖博之友會,於今年3月10和14日分別在高雄和臺北參與舉辦了紀念圖博抗暴五十週年的遊行,也促成了高雄市與臺南市圖博日的訂定與相關紀念活動。待會也請她來談一談,她看了《金色的聖山》之後的想法。講到這裡,我想到袁紅冰教授的英雄人格哲學,這是他寫作的一個重要精神動力來源,袁紅冰教授的英雄人格哲學是美與情感的聖經,他強調要重新喚起能夠值得女人愛戀的英雄人格。
再來是跋熱.達瓦才仁先生。他是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代表,同時也是臺灣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的董事長。達瓦才仁先生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中共統治之下成長的一代,他的漢語和寫作都非常流利、非常好,而且他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文獻典籍,曾經非常地認真研究過,特別是有關西藏方面資料的耙梳。儘管他寫的東西或是他說的國語比我們臺灣很多人還要流利、比很多漢人還要流利,不過他血脈中流的是藏人的血,他要用漢人的方式讓漢人或中國人、臺灣人能夠更了解圖博跟西藏的文化和發展現狀。他是漢藏和臺藏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樑,我們很高興臺灣能有這樣的朋友,達賴喇嘛派他來臺灣作為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是我們大家的福氣。
跋熱.達瓦才仁先生是翻越喜馬拉雅山逃亡至印度的,西藏的生活及逃亡的過程,相信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山或書中所描述的金色聖山崗仁波欽山,這些景象或記憶,對他而言應當是非常深刻的!這不單單是一種景色的美,更包含非常深刻的苦難與痛苦經驗,以及對於故鄉的懷念。袁紅冰用金色的聖山作為象徵,對於西藏人民追求自由的崇高人格與信念表示了崇敬。待會要請他來發言。
前面簡短對來賓的介紹就到此告一個段落,我想就按照順序,先請周美里小姐,再請達瓦,最後再請袁紅冰先生來做一個報告。
感動人心的力量
周美里:謝謝主持人,其實我來這本來是很想聽作者來跟我們分享他寫這本小說的感覺,不過先讓我來講,所以待會可能會有很多沒有非常切題的地方。我要先感謝第一個是袁紅冰先生能夠用這個主題來創作這個小說,我想這個是對漢人和藏人之間互相了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過去尤其在臺灣,臺灣人對圖博的印象過去很早以來第一個停留的就是在宗教,大家好像談到圖博只想到藏傳佛教,想到宗教。慢慢地這幾年來,越來越多人關心圖博的議題,再加上這一兩年來圖博境內發生相當多的事,所以我們開始有更多的人關心他們人權的議題、文化的問題,所以我們很高興也很感謝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這幾年來對於圖博相關的議題有相當多的出版。從最早傅正明的西藏流亡詩學的探討《詩從雪域來──西藏流亡詩人詩情的探討》,還有一些像茉莉的著作《山麓那邊是西藏》 初步介紹有關圖博議題的書。有關2008年西藏314的抗暴,允晨也出了一本唯色寫的書《鼠年雪獅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紀》。這方面議題的著作相當地多。我很高興從這些詩及較政治性的主題發展到小說。大家都知道小說可能是所有書籍當中感染力最強的,它的感情是很豐富且直接的。在臺灣的社會中,我們希望用各種不同的角度與想法,用小說或其他的形式,促進漢人與藏人間相互的了解。所以《金色的聖山》能夠出版讓我非常高興,我相信讓臺灣的讀者用小說的形式來了解圖博人真正有血有淚的感情,也可以了解漢人和藏人之間的事。
最近中國的出版界出了一些類似像冒險犯難的筆法,利用圖博這種神祕性寫了一些有如好萊塢式的小說,如《藏地密碼》等,這種消費圖博人的行為,更讓我們感到《金色的聖山》這本書的可貴。不是用好萊塢式的方法把圖博描繪成神祕的、具有神奇力量的而用以寫成好萊塢式的冒險小說。所以今天很開心很高興《金色的聖山》在臺灣能夠跟臺灣的讀者見面。
袁先生和允晨應該是選擇了一個很特別的時機,大家可能也有看到這幾天兩岸的世界佛教論壇正從無錫移師到臺灣,昨天在臺灣開始舉行。3月28日中共還宣布訂定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並且發表了一個《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書。這幾天我還看到中共排山倒海的、各式各樣攻擊達賴喇嘛的言論,各式各樣攻擊圖博人的言論,更讓我感受到中共的政權正傾全力在攻擊、企圖要滅絕圖博人的文化、宗教及精神,我覺得這個是這幾天感受特別深的。例如像他們所提出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書裡面,通篇有七個章節,沒有一個章節提到宗教的問題。然而圖博人的精神與文化當中宗教一直是他們最重要的核心的文化與價值,但中共所提出的白皮書當中沒有一個章節有提到這部份,可見中國政權統治圖博是相當心虛的,在面對圖博的問題當中,他們其實是完全不敢正視圖博宗教自由的議題,所以今天在這個時機點出版此一小說也有相當大的意義。我想我就說明到此,待會袁先生會有更精采的要與我們分享,謝謝。
揭示真相,功德無量
跋熱.達瓦才仁: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興今天我們在這可以看到《金色的聖山》在臺灣的再版。更早,在前年,我就看過這本書,且是從頭到尾都閱讀過。就像剛才建元先生所談到的,我對中文裡面有關西藏的描寫都是比較關注的,不論是歷史或是現在的。我看過很多描寫西藏的小說,就像美里剛剛所談到的,把西藏作為一種消費,把它作為一種好萊塢式的演義,其實,如果是好萊塢式的演義,對西藏來說還算是蠻善意的,至少,它還是把西藏做為一種比較平等的描述對象。
而在平常,或者說在西藏,我們常看到的幷不是這樣。記得我唸初級中學時,上課偷看一本叫《草原上的小姊妹》的小說,我很清楚地記得封面是一個女孩子騎在馬上揚鞭抽打一隻老鷹,那個老鷹要把公社的小羊叼走,小姊妹在保護公社的羊,是這樣一部很制式的小說。偷看小說被老師發現後,老師拿著沒收的小說,卻感觸萬分地對我們說,人家蒙古有自己的小說,我們西藏卻沒有一本自己的小說。他當時這麼說,所以我感到我們西藏沒有自己的小說,就到處去找,後來找到一本,叫《金色的太陽》,內容是描寫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怎麼救苦救難,其中我還看到很多對西藏宗教文化的一些具體的描述。因為當時中共還在西藏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些有關宗教的東西,即使最基本的像是袈裟,我根本就沒見過,只有聽過,但不知它的樣子,還有像是「卍」字符號,這些符號我都聽過但從來沒見過,社會上已經完全沒有這些宗教的符號,我只是聽父母講過。而這本書裡面對這些就有一些描述,這些就是我對西藏自己的文化第一次通過文字描述有較具體明確的認識,相對於口頭的流傳,我還是相信文字的「正式」的描述,當然,後來發現這些描述和認識都是錯的,都是作者自己在那裡亂掰、瞎編的。
電影也一樣,那時有一部電影叫《農奴》,我父母和許多的西藏人都很喜歡去看,每次放映都要去看,但是他們只看前一段然後就離開了,後半段場裡就剩沒多少人,我覺得奇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因為前一半是描寫西藏宗教原來的黑暗,它有很多宗教場合的描述,比如說喇嘛吹長號,喇嘛在一起誦經,還有經典與很多佛像,我們的父母去看的就是這些,他們記憶中最神聖的東西,而在現實中沒有,所以他們不管內容描寫什麼,他們就只看這些場景,這些看完,後面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事情他們就不看回家了。所以說從我們的角度而言,我們接受西藏文化的途徑,除了家庭的教育,那些來自文字和電影的認識都是從這種很奇怪的方式得到的,就是說,當時的我們只能通過旨在貶底我們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去了解和認識自己的文化,而沒有其他的途徑。到後來,特別是像我們這些說中文的、學中文的,你叫我講像是《戰國策》、《左傳》那些我都可以一條一條列出來,但是你讓我講西藏自己的文化就什麼也講不出來。我年輕時甚至想過,如果我們西藏有詩歌那該有多好,那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西藏的詩歌不僅非常地豐富,而且早在七百年前就已經有了完整的詩歌理論體系,但所有這一切我們完全不知道,在社會上根本看不到藏文和詩歌。因此,我真的以為西藏沒有詩歌,西藏的藏文是用來寫佛經的,要不然就是民歌,而民歌裡都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我們就是這樣去學習中文,然後從中文中去接觸所謂的西藏民族文化,其方式是如此迂迴曲折,直言之,通過中文傳遞給我們的訊息都是已經被扭曲或胡編亂造到面目全非的內容。
在中文的書籍裡第一個較為真實、並且以漢人的角度談論西藏的著作的,應該是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運》,小說則應該就是《金色的聖山》。這本書對西藏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有描述。漢、藏人,與一些信徒與不信教的,還有一些中共官員,西藏人作為中共官員的,他們內心的那些痛苦與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都有一些很清楚的描述。這讓我想到剛剛談論到的世界佛教論壇,有一位中共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他說:「我非常感謝共產黨擦亮我的眼睛,使我知道了怎麼回事」,這句話很讓人回味,如果聽得懂共產黨的語言,這說明之前他有一段時間他的眼睛是不亮的,是共產黨教育他使他亮了,至於共產黨如何讓他的眼睛明亮,任何經歷過專制統治的人都會心知肚明。如果再回憶一下去年3月西藏發生抗暴時,中共沒有把中共指定的班禪推出來,也許那時他的眼睛可能就沒有亮,現在他亮了,就不得不出來說一些話。就算是中共自己任命的西藏人官員,可能也不願意去說這些話。
另外一個例子是第十七世噶瑪巴大寶法王烏金聽列多傑,他逃到印度時很多人都問他為何要逃出來?他說:「第一、我是一個噶瑪巴,我光有這個名字沒有這個宗教的傳承是不行的,但西藏所有法脈的傳承都在境外,我要成為噶瑪巴只有接觸這些法脈,但是要邀請那些高僧到西藏,中共不允許,所以我只好跑出來。第二、我過幾年就十八歲了,逃出來時十六歲,到十八歲中共可能就會讓我擔任一些政治職務,這個職務我不得不去當,當了之後就不得不說一些話,特別是攻擊達賴喇嘛的話,這是我所不願的,所以我只好逃出來」。這就是西藏人的選擇,要不是必須背棄信仰,不然就是選擇逃亡或進監獄。這就是西藏的現狀,面對這種現狀的不僅僅是高僧,一般的幹部、工作人員,所有的人都是如此。這些方面,這本小說都有最真實的描繪,它所描述都是很曲折的,它描繪這些藏人官員是怎樣的心態,它描述他們怎樣去面對不同人之誤解或攻擊,或是中國人對他們的不信任等。所以希望透過這些小說,或是像王力雄這種記事性的描述,至少讓更多的中文讀者,看到西藏人的狀況是如何。如果能這樣從西藏人的角度出發,如書中描述的一些漢藏之間的關係,真的是功德無量。
這個世界上有幾千個民族,與西藏人最親近的就是蒙古人了。在西藏的社會裡,並沒有把蒙古人看成是其他的不同民族,就像西藏人有康巴人、安多人一樣,說到蒙古人,感覺也是類似的,在西藏流亡社會,蒙古人和西藏人是同樣對待的,蒙古人不算是外國人。除了蒙古人,和西藏民族最接近的應該就是漢族了,漢藏民族之間有很多的相通點,這兩個民族不論從歷史或現實面去探討,根本就沒必要變成現在的這種狀態,目前所有的現狀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所以通過這些中文,不論是史詩性的、或是小說的記載方式,讓雙方之間有更深的了解,從而去消弭中共所造下的這些孽,用以實現真正所謂的和諧,實現兩個民族之間的和睦相處,延續雙方在歷史上長久建立的生活經驗、價值觀或其他方面的共存共榮關係,彌補缺失,以使兩個民族得以久遠地共處,互相尊重、補充,達到共贏。這些都是符合兩個民族的,我相信這些書肯定會對這方面產生非常積極的意義,謝謝。
虛實之間
曾建元:謝謝達瓦。最後我們很期待袁紅冰教授來報告這個書。這本書帶有點自傳的色彩,其中的主角白帆,我就看到很多袁教授本身的影子。這本書究竟是虛構或哪些是真實的,我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到有許多值得玩味之處。達瓦談到書中有許多用文學的筆法描述西藏真實的狀況,例如側身共產黨的高官內心的掙扎與痛苦。本書中所提到的人物多仁‧丹增班覺,其實是影射曾任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後來擔任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晉美。中藏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當時的西藏代表團,就是由阿沛.阿旺晉美率領的。他於1951年在北京,在幾乎被隔離與西藏噶登頗章王朝嘎廈政府任何聯繫與被軟禁的狀況下,被迫簽下這個協議,後來此份協議被共產黨撕毀,阿沛.阿旺晉美則一直在北京卵翼下擔任高官。世人對於〈十七條協議〉簽訂的狀況一直不甚了解,但最後則是由阿沛.阿旺晉美親自揭開了整個簽訂的過程。他在1989年7月在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第5屆第2次會議上發言,使外界能充分地得知,他們是在一個何等無奈的狀態下簽訂此一協議的。當時的西藏代表為了規避責任,只好宣稱是以自己的名義來簽訂,並不代表當時的西藏政府。我們可以看到袁紅冰教授在此本小說中所描寫的阿沛.阿旺晉美這樣一個怯懦而矛盾的形象。然而,我在書中人物多仁‧丹增班覺身上,彷彿也看見第十世班禪喇嘛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的影子。多仁‧丹增班覺生活在北京被共產黨包圍的環境中,在自己內心當中為維護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傳統,而與共產黨的無神論激烈掙扎,不時地面對良心的譴責,但他有一個靈魂聖潔而地位尊貴有如十世班禪女兒堯西‧班‧仁吉旺姆公主的女兒珠牡,珠牡最後則與多仁‧丹增班覺的情婦益西卓瑪於出家時被紅衛兵強迫於甘丹寺前與僧人格勒公開性交而生下的兒子僧人貝吉多傑,在雅魯藏布江北的枯黑色山峰,為絕美的激情而真誠勇敢地焚身獻祭。這些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情節,《金色的聖山》中都有著非常深刻而顏色斑斕光彩燦爛的描寫,我對之感到非常地震撼。接下來就請袁紅冰教授親身來談談這本小說。
為藏人生命的極致之美而吟詠
袁紅冰:謝謝大家。首先要感謝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文字編輯及美術編輯,他們將這本書作成如藝術品般,真是很感謝。剛才坐在這裡的時候,我腦子裡突然想起第一次走上西藏,追隨那鐵褐色的高原上茫茫的風塵漫遊之時的感覺,當時感覺是走在一部悲愴的史詩當中。那片土地曾於1959年發生藏人英雄的大起義中,被那些英雄們的血浸透;那片土地上有很多的白骨,很多生命的殘骸。後來充份了解了西藏之後,我發現屬於藏人的苦難,並不僅是死亡、鮮血及白骨,藏人的苦難,更深刻的是其心靈所遭受的苦難與悲劇。一個鐵血的強權設置了精神與思想的牢籠,將藏人的心靈囚禁於此。藏人所發出的每一聲反抗、每一次抗爭中的呼喊,都是美麗聖潔的靈魂被禁錮在黑暗的鐵牢中所發出的悲愴呼喚。
有人問我,你寫的究竟是真實抑或虛構?我為了創作這本書,查閱了大量的檔案與資料,並且結交許多藏人朋友,與阿沛.阿旺晉美先生身邊的友人有著很深刻的接觸——當然我不便說出他們的身份。當時我思考該如何著筆此本創作,我也可以像寫歷史一樣,因手中握有許多相關資料。但是我覺得單憑歷史簡單的描繪,不足以表達藏人的苦難。我可以列舉在1959年藏人大起義中,有多少藏人犧性,西藏有多少的寺院被中共暴政摧毀,中共在寺廟裡安排了多少宗教特務;但這些數字在藏人的苦難面前顯得如此蒼白,所以我選擇用文學的筆觸來創作這本著作。
有人問我,這本書到底是怎樣的書?是小說還是詩歌,是詩還是哲學著作?我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本書的創作形式是由我對藏人心靈的體驗所決定的。有的人說這不是一本小說,因為它不是傳統的小說形式——就像編輯小姐寫的「開啟了全新的小說敘述」。藏人是一個充滿詩意的民族,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與低地人不同,他們沒有那麼多對物性、物質的慾望,但是他們有很多心靈的慾望,他們喝了酒就會笑得像一團火燄般。我記得有一位前世的達賴喇嘛就是一位詩人,他寫的詩那麼美。與其他宗教相比,藏傳佛教本身極為哲學化。透過對前世達賴喇嘛的詩之閱讀,我感覺到藏人既有一顆充滿哲理的心;又有一顆充滿詩意的心。
我於七次入藏、於藏人的交流當中,感覺到他們是最善良的民族,而這樣的民族卻身處於痛苦之中。小說裡寫了許多藏人具體的痛苦。我看過一本書,它僅從現象上去批評藏人如何落後、衣著不整等,當人們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藏人時,我覺得他們那骯髒、以物性為標準的心,根本無法解理一個把整個人生當作一次朝聖之旅的民族,他們的心中追求的是什麼!在現今生命普遍在物慾中腐爛的時代,藏人的這種情懷,是屬於整個人類的精神財富。
有的人說我是同情藏人,錯了!有的人說我是同情弱小的民族,更錯了!
不是我同情藏人,是我被藏人如此美麗的人格深深地感動!不感動我,我不會去寫,我感動得不足以形容,這震撼了我。我一定要讓藏人的苦難,透過我的筆,成為自由的史詩與生命的哲理,我可能才完成此生活著的一點意義。
另外,說到藏人是個弱小的民族,也許從現在人數上看藏人的確是少了些,但是藏人在歷史上是極其強悍的民族。吐蕃王國時代,藏人曾開啟強大的唐帝國的城門,迫使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女人——文成公主送至西藏和親。從前如此強大的民族,他們曾經像那鐵褐色山高原的風暴盤旋呼嘯,但他們信奉、皈依了佛教。在藏傳佛教中,風暴平息了,大海平靜了,藏族原本強悍的銳氣變成一個悲憫蒼生的宗教存在。這個宗教的存在到底有何意義和價值?我之所以認為藏傳佛教為人類保存了最後的精神價值,理由之一是祂創造出了當今世界上,最高貴聖潔美麗而又自由的族群,那就是藏人。走進西藏,當目光與藏族的少女對視時會驚覺,黑色,是世界上最燦爛的色彩。其人格是文化和文明的總結,也是藏人最主要的象徵。然而這樣的文化卻處於現實的危險之中。我有時覺得自己太沒有能力了!
我在書中最後寫到:「我沒有辦法幫藏人做更多的事情,我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讓那些在強權之下為了堅持自己精神的信念而死去的這些美麗高貴的男女,通過我的書能夠重新復活,獲得不朽的存在形式」。我只能做到如此。但我多麼希望能看到流亡的藏人能夠重返自己的故鄉,能夠重新在那片高原上展開自己神聖的心靈之旅。我不知道我能為藏人做什麼,有的人說我做了很多,但我只能用筆來寫這本書,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啊!
當整個世界尚處於黑暗之中時,西藏的雪山燃燒起第一道朝霞;當整個世界皆沉入夜色當中時,西藏高原的雪山仍閃耀著最後一抺晚霞。那是一個充滿猶如金色皇冠般雄偉壯麗的雪山土地。東亞大陸、南亞次大陸、東南亞等所有偉大的河流,都是發源自這片高原。它養育了印度與中華兩個偉大的文化。我們現在該做的,是要思索應如何回饋這片土地。我們為何會允許一個鐵血權力把如此聖潔的高地變成一個心靈的地獄?那些政治家、領袖、商人們,還有那些所謂的宗教領袖們,你們不感到恥辱嗎?
鑒於時間的關係就不多說了。我很感謝編輯把這段話摘出來,我唸一遍作為最後的結尾:「我走上這荒涼的高原是為了尋找美麗、真實、聖潔的生命。我找到了,但他們又離開了我……。索朗白牡、達娃、珠牡和貝吉多傑,他們都默默地消失了,他們的身影被鐵褐色荒原上那漫遊萬里的青銅色長風吹散了,但我要使他們消失於無邊荒涼中的美麗生命,成為流傳千古的詩;成為萬年不朽的歌;成為金色日球的高貴魂魄!」
謝謝大家。
答問:西藏文化在流亡中
曾建元:謝謝袁老師。他本來是一位法學的教授,但他則選擇以小說的形式來表達他對於西藏問題的看法。他剛剛的發言當中一再提到,我們該要如何去喚回我們對自由精神作為人的本質的一種力量,而他至少認為文學感性的形式,可以去感動人心,對於人之情感的謳歌所散發的力量,會比歷史學、法學或政治學的那種學術文字更來得大。
接下來還有一段時間,各位讀友可以跟袁教授進一步提問,大家可以就看了這本書,──還沒看過這本書也沒關係,有任何問題與想法自由表達,最後再請袁教授做綜合答覆。現在歡迎各位發言。
蘇明(民主中國陣線加拿大分部副主席):達瓦您好,文革時期,不光是西藏的文化、甚至整個中華文化都受到破壞。目前中國政府對西藏宗教有哪些有限制?
跋熱.達瓦才仁:剛剛你談到一個概念,很多人都會說文革時不僅僅是西藏,中國的文化也遭遇到破壞,其實這不是完全正確的。文化有新陳代謝,它有承載的問題。中國的文化都是用中文承載的,中國的共產主義也是一種文化。在五四運動中,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知識份子許多主張西化,這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它使部份的傳統文化自動消滅,但這一過程卻並非來自外來的壓迫。傳統的中華文化自動消滅的同時,也吸收了西方的東西,所以對中國來說,其實是消滅了一部份,吸收了一部份,它並沒有全部被消滅,或者說只是一種新陳代謝,汰舊換新,至於後來發現汰換的不太對,那是後知後覺,從一開始中國知識份子都要去擁抱西方的文化,並從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那是一種本民族菁英份子自己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一種外力消滅。但西藏卻恰恰相反,不存在任何的汰舊換新,完全是赤裸裸的文化滅絕,就如我剛剛所言,包括西藏民族的文字、符號等通通都沒有了,不被允許存在,同時卻被強迫去接觸和學習異民族的文字和文化,完全是暴力脅迫,與西藏民族的選擇不僅沒有任何的關係,而且是恰恰相反的,所以這兩個完全不是同一個問題,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現在西藏的宗教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樣的地方,就如剛剛所談的,西藏的宗教是一個哲學的宗教。一個西藏的僧人,就像噶瑪巴他必須要逃到國外去學習,並不是他出家了就是噶瑪巴。從西藏人的角度而言,他出家必須要掌握佛教的經典理論,而這些你必須要學習十幾年,最少也要幾年,而且這種學習都要進行相互的切磋辯論,所以佛教有一個概念就是佛法就像是對金子的磨鍊一樣,你可以用各種方式不斷地去驗證祂,因此佛教是最辯證的。辯證法以前我自己讀過,我拿去與佛教僧侶討論,發現這些在大學裡面被認為是很高深的東西,在佛法裡面其實是最基本的課程。這樣一個高深的內容必須要經過十幾年的學習,最少要學十幾年,一般都要二十幾年,而且這種學習是要在各教派之間互相進行辯論探討的。中共在西藏,對宗教的允許是屬於僅僅允許你求神拜佛的,允許你拜拜,中共把佛教貶為求神拜佛的民間信仰的層次,把僧人視為類似神漢、巫婆的角色;但在西藏人的角度,僧人的角色並非如此,他是傳播佛法的,是一個非常高尚、非常有學問的工作,他這種學習必須要經過十幾年的工夫,但這種條件和環境完全不存在,我所謂完全不存在,是指所有都沒有了,即是我所說的,西藏的法脈已不在西藏,在流亡中。
說到修持佛法,就有非常多的限制,比如說一個西藏人要出家,則受到名額的管制,中國共產黨規定一個寺院的編制人數,大的寺院是五百人,中的寺院是一百人。但所有的寺院幾乎都會超編,因為出家人很多,在這裡,你的出家人身分,並非取決於你是否信仰宗教、是否受戒、寺院是否願意接受你等宗教因素,而是取決於中共政府宗教局黨官是否認定你是一個出家人,或者是寺院裡有無缺額,比如說必須等有人還俗或有人往生了,你才可以補上。如果等不到這些而你自己去出家,共產黨隨時都可以抓你,並以詐騙罪來「依法」判你,因為你一旦出家就會接受到別人的供養,而當局可以認定你冒充宗教人士,欺騙信徒。所以,你的出家身分是由共產黨幹部決定的,他們不承認,你私自出家就可以判你有罪,也因此,迫使很多的僧人逃亡到國外。現在還有一個叫愛國主義教育,要求所有的出家人都必須要攻擊達賴喇嘛,但西藏的宗教確信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在西藏的轉世,是西藏的保護神,你如果攻擊了達賴喇嘛,你就不會是一個完整的僧人,根本再也談不上修行的問題;但若不攻擊的話,則連僧人都當不成,這就是西藏宗教界所面臨的問題。哪怕是只是接受戒律的傳承,這個傳承也是不完整的,因為你必須要攻擊自己的上師。一般的西藏人不充許信仰達賴喇嘛,但他不信仰中共指定的班禪喇嘛也是不行,你必須要信。所以在西藏,信仰似乎變成了中共官員手中的玩具,他要你信,你不信也得信,他不許你信,你信也不行。這就是西藏目前宗教的現狀。所以西藏現在其實沒有宗教,只有一種祈福禳災的神漢巫婆這種規模、這種層次的宗教活動,而沒有真正佛法的傳承。





作者;袁紅冰
出版時地: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
主辦: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2009年3月31日上午10:30~12:00
地點:臺北市臺大校友會館三樓C室
主持: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臺灣圖博之友會監事)
主講:袁紅冰(澳大利亞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首席委員)
與談:周美里(臺灣圖博之友會會長)
跋熱.達瓦才仁(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整理:楊惠羽(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研究生)
校訂:曾建元
曾建元:各位讀友早安,今天是袁紅冰先生《金色的聖山》這本書的允晨版的新書發表會,非常歡迎各位能夠蒞臨今天的會場,首先跟各位介紹今天出席的來賓。我想袁紅冰教授大家都很熟悉了,他為了寫《金色的聖山》這本書,七次出入西藏,我先對他做一點簡單的介紹,最後再來聽他寫作本書的想法。
袁紅冰教授1952年出生於內蒙古自治區,後來在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就學,
與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是同系的前後期同學,一起上過課,但命運不同。袁紅冰本科畢業之後留在北大唸法律學碩士,取得學位之後留下來任教,擔任有關訴訟法方面的課程。在1989年六四之時,他組織了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聲援學生,導致六四之後一度被迫離開教職,在一連串的司法和學術上的迫害之後,最後他被流放到貴州,後來在貴州師範大學擔任法學院長。在貴州期間他完成了他幾本重要小說的手稿,《金色的聖山》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為了讓他的自由創作能順利地問世,袁教授選擇於2004年7月利用到澳洲訪問的機會投奔自由。連同《金色的聖山》在內的幾本重要創作,都是在非常辛苦的、身體與精神皆處於苦難磨鍊的環境當中祕密粹煉完成的。
《金色的聖山》於2005年也曾在臺灣由博大出版社出版過,這次有機會在臺灣的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支持下再版,表示這本書在臺灣和自由世界裡擁有非常多的讀者。我們都非常關心西藏/圖博的問題,特別是對臺灣而言,我們對圖博的民族苦難感同深受,因為雙T(Taiwan, Tibet)臺灣與圖博都受到中國共產黨政權在全世界各處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可以看到袁教授身為一個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如此地關心被中共壓迫的弱勢民族的命運,令我非常佩服。
接下來介紹周美里小姐,她是臺灣圖博之友會會長,她算是圖博的媳婦,他的先生凱度頓珠先生是西藏流亡人民議會的議員。周美里小姐這幾年促進臺灣民間與西藏人民之間的認識,做了非常大的貢獻,如發起成立了臺灣圖博之友會,於今年3月10和14日分別在高雄和臺北參與舉辦了紀念圖博抗暴五十週年的遊行,也促成了高雄市與臺南市圖博日的訂定與相關紀念活動。待會也請她來談一談,她看了《金色的聖山》之後的想法。講到這裡,我想到袁紅冰教授的英雄人格哲學,這是他寫作的一個重要精神動力來源,袁紅冰教授的英雄人格哲學是美與情感的聖經,他強調要重新喚起能夠值得女人愛戀的英雄人格。
再來是跋熱.達瓦才仁先生。他是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代表,同時也是臺灣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的董事長。達瓦才仁先生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中共統治之下成長的一代,他的漢語和寫作都非常流利、非常好,而且他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文獻典籍,曾經非常地認真研究過,特別是有關西藏方面資料的耙梳。儘管他寫的東西或是他說的國語比我們臺灣很多人還要流利、比很多漢人還要流利,不過他血脈中流的是藏人的血,他要用漢人的方式讓漢人或中國人、臺灣人能夠更了解圖博跟西藏的文化和發展現狀。他是漢藏和臺藏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樑,我們很高興臺灣能有這樣的朋友,達賴喇嘛派他來臺灣作為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是我們大家的福氣。
跋熱.達瓦才仁先生是翻越喜馬拉雅山逃亡至印度的,西藏的生活及逃亡的過程,相信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山或書中所描述的金色聖山崗仁波欽山,這些景象或記憶,對他而言應當是非常深刻的!這不單單是一種景色的美,更包含非常深刻的苦難與痛苦經驗,以及對於故鄉的懷念。袁紅冰用金色的聖山作為象徵,對於西藏人民追求自由的崇高人格與信念表示了崇敬。待會要請他來發言。
前面簡短對來賓的介紹就到此告一個段落,我想就按照順序,先請周美里小姐,再請達瓦,最後再請袁紅冰先生來做一個報告。
感動人心的力量
周美里:謝謝主持人,其實我來這本來是很想聽作者來跟我們分享他寫這本小說的感覺,不過先讓我來講,所以待會可能會有很多沒有非常切題的地方。我要先感謝第一個是袁紅冰先生能夠用這個主題來創作這個小說,我想這個是對漢人和藏人之間互相了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過去尤其在臺灣,臺灣人對圖博的印象過去很早以來第一個停留的就是在宗教,大家好像談到圖博只想到藏傳佛教,想到宗教。慢慢地這幾年來,越來越多人關心圖博的議題,再加上這一兩年來圖博境內發生相當多的事,所以我們開始有更多的人關心他們人權的議題、文化的問題,所以我們很高興也很感謝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這幾年來對於圖博相關的議題有相當多的出版。從最早傅正明的西藏流亡詩學的探討《詩從雪域來──西藏流亡詩人詩情的探討》,還有一些像茉莉的著作《山麓那邊是西藏》 初步介紹有關圖博議題的書。有關2008年西藏314的抗暴,允晨也出了一本唯色寫的書《鼠年雪獅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紀》。這方面議題的著作相當地多。我很高興從這些詩及較政治性的主題發展到小說。大家都知道小說可能是所有書籍當中感染力最強的,它的感情是很豐富且直接的。在臺灣的社會中,我們希望用各種不同的角度與想法,用小說或其他的形式,促進漢人與藏人間相互的了解。所以《金色的聖山》能夠出版讓我非常高興,我相信讓臺灣的讀者用小說的形式來了解圖博人真正有血有淚的感情,也可以了解漢人和藏人之間的事。
最近中國的出版界出了一些類似像冒險犯難的筆法,利用圖博這種神祕性寫了一些有如好萊塢式的小說,如《藏地密碼》等,這種消費圖博人的行為,更讓我們感到《金色的聖山》這本書的可貴。不是用好萊塢式的方法把圖博描繪成神祕的、具有神奇力量的而用以寫成好萊塢式的冒險小說。所以今天很開心很高興《金色的聖山》在臺灣能夠跟臺灣的讀者見面。
袁先生和允晨應該是選擇了一個很特別的時機,大家可能也有看到這幾天兩岸的世界佛教論壇正從無錫移師到臺灣,昨天在臺灣開始舉行。3月28日中共還宣布訂定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並且發表了一個《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書。這幾天我還看到中共排山倒海的、各式各樣攻擊達賴喇嘛的言論,各式各樣攻擊圖博人的言論,更讓我感受到中共的政權正傾全力在攻擊、企圖要滅絕圖博人的文化、宗教及精神,我覺得這個是這幾天感受特別深的。例如像他們所提出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書裡面,通篇有七個章節,沒有一個章節提到宗教的問題。然而圖博人的精神與文化當中宗教一直是他們最重要的核心的文化與價值,但中共所提出的白皮書當中沒有一個章節有提到這部份,可見中國政權統治圖博是相當心虛的,在面對圖博的問題當中,他們其實是完全不敢正視圖博宗教自由的議題,所以今天在這個時機點出版此一小說也有相當大的意義。我想我就說明到此,待會袁先生會有更精采的要與我們分享,謝謝。
揭示真相,功德無量
跋熱.達瓦才仁: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興今天我們在這可以看到《金色的聖山》在臺灣的再版。更早,在前年,我就看過這本書,且是從頭到尾都閱讀過。就像剛才建元先生所談到的,我對中文裡面有關西藏的描寫都是比較關注的,不論是歷史或是現在的。我看過很多描寫西藏的小說,就像美里剛剛所談到的,把西藏作為一種消費,把它作為一種好萊塢式的演義,其實,如果是好萊塢式的演義,對西藏來說還算是蠻善意的,至少,它還是把西藏做為一種比較平等的描述對象。
而在平常,或者說在西藏,我們常看到的幷不是這樣。記得我唸初級中學時,上課偷看一本叫《草原上的小姊妹》的小說,我很清楚地記得封面是一個女孩子騎在馬上揚鞭抽打一隻老鷹,那個老鷹要把公社的小羊叼走,小姊妹在保護公社的羊,是這樣一部很制式的小說。偷看小說被老師發現後,老師拿著沒收的小說,卻感觸萬分地對我們說,人家蒙古有自己的小說,我們西藏卻沒有一本自己的小說。他當時這麼說,所以我感到我們西藏沒有自己的小說,就到處去找,後來找到一本,叫《金色的太陽》,內容是描寫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怎麼救苦救難,其中我還看到很多對西藏宗教文化的一些具體的描述。因為當時中共還在西藏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些有關宗教的東西,即使最基本的像是袈裟,我根本就沒見過,只有聽過,但不知它的樣子,還有像是「卍」字符號,這些符號我都聽過但從來沒見過,社會上已經完全沒有這些宗教的符號,我只是聽父母講過。而這本書裡面對這些就有一些描述,這些就是我對西藏自己的文化第一次通過文字描述有較具體明確的認識,相對於口頭的流傳,我還是相信文字的「正式」的描述,當然,後來發現這些描述和認識都是錯的,都是作者自己在那裡亂掰、瞎編的。
電影也一樣,那時有一部電影叫《農奴》,我父母和許多的西藏人都很喜歡去看,每次放映都要去看,但是他們只看前一段然後就離開了,後半段場裡就剩沒多少人,我覺得奇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因為前一半是描寫西藏宗教原來的黑暗,它有很多宗教場合的描述,比如說喇嘛吹長號,喇嘛在一起誦經,還有經典與很多佛像,我們的父母去看的就是這些,他們記憶中最神聖的東西,而在現實中沒有,所以他們不管內容描寫什麼,他們就只看這些場景,這些看完,後面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事情他們就不看回家了。所以說從我們的角度而言,我們接受西藏文化的途徑,除了家庭的教育,那些來自文字和電影的認識都是從這種很奇怪的方式得到的,就是說,當時的我們只能通過旨在貶底我們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去了解和認識自己的文化,而沒有其他的途徑。到後來,特別是像我們這些說中文的、學中文的,你叫我講像是《戰國策》、《左傳》那些我都可以一條一條列出來,但是你讓我講西藏自己的文化就什麼也講不出來。我年輕時甚至想過,如果我們西藏有詩歌那該有多好,那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西藏的詩歌不僅非常地豐富,而且早在七百年前就已經有了完整的詩歌理論體系,但所有這一切我們完全不知道,在社會上根本看不到藏文和詩歌。因此,我真的以為西藏沒有詩歌,西藏的藏文是用來寫佛經的,要不然就是民歌,而民歌裡都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我們就是這樣去學習中文,然後從中文中去接觸所謂的西藏民族文化,其方式是如此迂迴曲折,直言之,通過中文傳遞給我們的訊息都是已經被扭曲或胡編亂造到面目全非的內容。
在中文的書籍裡第一個較為真實、並且以漢人的角度談論西藏的著作的,應該是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運》,小說則應該就是《金色的聖山》。這本書對西藏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有描述。漢、藏人,與一些信徒與不信教的,還有一些中共官員,西藏人作為中共官員的,他們內心的那些痛苦與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都有一些很清楚的描述。這讓我想到剛剛談論到的世界佛教論壇,有一位中共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他說:「我非常感謝共產黨擦亮我的眼睛,使我知道了怎麼回事」,這句話很讓人回味,如果聽得懂共產黨的語言,這說明之前他有一段時間他的眼睛是不亮的,是共產黨教育他使他亮了,至於共產黨如何讓他的眼睛明亮,任何經歷過專制統治的人都會心知肚明。如果再回憶一下去年3月西藏發生抗暴時,中共沒有把中共指定的班禪推出來,也許那時他的眼睛可能就沒有亮,現在他亮了,就不得不出來說一些話。就算是中共自己任命的西藏人官員,可能也不願意去說這些話。
另外一個例子是第十七世噶瑪巴大寶法王烏金聽列多傑,他逃到印度時很多人都問他為何要逃出來?他說:「第一、我是一個噶瑪巴,我光有這個名字沒有這個宗教的傳承是不行的,但西藏所有法脈的傳承都在境外,我要成為噶瑪巴只有接觸這些法脈,但是要邀請那些高僧到西藏,中共不允許,所以我只好跑出來。第二、我過幾年就十八歲了,逃出來時十六歲,到十八歲中共可能就會讓我擔任一些政治職務,這個職務我不得不去當,當了之後就不得不說一些話,特別是攻擊達賴喇嘛的話,這是我所不願的,所以我只好逃出來」。這就是西藏人的選擇,要不是必須背棄信仰,不然就是選擇逃亡或進監獄。這就是西藏的現狀,面對這種現狀的不僅僅是高僧,一般的幹部、工作人員,所有的人都是如此。這些方面,這本小說都有最真實的描繪,它所描述都是很曲折的,它描繪這些藏人官員是怎樣的心態,它描述他們怎樣去面對不同人之誤解或攻擊,或是中國人對他們的不信任等。所以希望透過這些小說,或是像王力雄這種記事性的描述,至少讓更多的中文讀者,看到西藏人的狀況是如何。如果能這樣從西藏人的角度出發,如書中描述的一些漢藏之間的關係,真的是功德無量。
這個世界上有幾千個民族,與西藏人最親近的就是蒙古人了。在西藏的社會裡,並沒有把蒙古人看成是其他的不同民族,就像西藏人有康巴人、安多人一樣,說到蒙古人,感覺也是類似的,在西藏流亡社會,蒙古人和西藏人是同樣對待的,蒙古人不算是外國人。除了蒙古人,和西藏民族最接近的應該就是漢族了,漢藏民族之間有很多的相通點,這兩個民族不論從歷史或現實面去探討,根本就沒必要變成現在的這種狀態,目前所有的現狀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所以通過這些中文,不論是史詩性的、或是小說的記載方式,讓雙方之間有更深的了解,從而去消弭中共所造下的這些孽,用以實現真正所謂的和諧,實現兩個民族之間的和睦相處,延續雙方在歷史上長久建立的生活經驗、價值觀或其他方面的共存共榮關係,彌補缺失,以使兩個民族得以久遠地共處,互相尊重、補充,達到共贏。這些都是符合兩個民族的,我相信這些書肯定會對這方面產生非常積極的意義,謝謝。
虛實之間
曾建元:謝謝達瓦。最後我們很期待袁紅冰教授來報告這個書。這本書帶有點自傳的色彩,其中的主角白帆,我就看到很多袁教授本身的影子。這本書究竟是虛構或哪些是真實的,我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到有許多值得玩味之處。達瓦談到書中有許多用文學的筆法描述西藏真實的狀況,例如側身共產黨的高官內心的掙扎與痛苦。本書中所提到的人物多仁‧丹增班覺,其實是影射曾任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後來擔任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晉美。中藏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當時的西藏代表團,就是由阿沛.阿旺晉美率領的。他於1951年在北京,在幾乎被隔離與西藏噶登頗章王朝嘎廈政府任何聯繫與被軟禁的狀況下,被迫簽下這個協議,後來此份協議被共產黨撕毀,阿沛.阿旺晉美則一直在北京卵翼下擔任高官。世人對於〈十七條協議〉簽訂的狀況一直不甚了解,但最後則是由阿沛.阿旺晉美親自揭開了整個簽訂的過程。他在1989年7月在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第5屆第2次會議上發言,使外界能充分地得知,他們是在一個何等無奈的狀態下簽訂此一協議的。當時的西藏代表為了規避責任,只好宣稱是以自己的名義來簽訂,並不代表當時的西藏政府。我們可以看到袁紅冰教授在此本小說中所描寫的阿沛.阿旺晉美這樣一個怯懦而矛盾的形象。然而,我在書中人物多仁‧丹增班覺身上,彷彿也看見第十世班禪喇嘛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的影子。多仁‧丹增班覺生活在北京被共產黨包圍的環境中,在自己內心當中為維護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傳統,而與共產黨的無神論激烈掙扎,不時地面對良心的譴責,但他有一個靈魂聖潔而地位尊貴有如十世班禪女兒堯西‧班‧仁吉旺姆公主的女兒珠牡,珠牡最後則與多仁‧丹增班覺的情婦益西卓瑪於出家時被紅衛兵強迫於甘丹寺前與僧人格勒公開性交而生下的兒子僧人貝吉多傑,在雅魯藏布江北的枯黑色山峰,為絕美的激情而真誠勇敢地焚身獻祭。這些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情節,《金色的聖山》中都有著非常深刻而顏色斑斕光彩燦爛的描寫,我對之感到非常地震撼。接下來就請袁紅冰教授親身來談談這本小說。
為藏人生命的極致之美而吟詠
袁紅冰:謝謝大家。首先要感謝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文字編輯及美術編輯,他們將這本書作成如藝術品般,真是很感謝。剛才坐在這裡的時候,我腦子裡突然想起第一次走上西藏,追隨那鐵褐色的高原上茫茫的風塵漫遊之時的感覺,當時感覺是走在一部悲愴的史詩當中。那片土地曾於1959年發生藏人英雄的大起義中,被那些英雄們的血浸透;那片土地上有很多的白骨,很多生命的殘骸。後來充份了解了西藏之後,我發現屬於藏人的苦難,並不僅是死亡、鮮血及白骨,藏人的苦難,更深刻的是其心靈所遭受的苦難與悲劇。一個鐵血的強權設置了精神與思想的牢籠,將藏人的心靈囚禁於此。藏人所發出的每一聲反抗、每一次抗爭中的呼喊,都是美麗聖潔的靈魂被禁錮在黑暗的鐵牢中所發出的悲愴呼喚。
有人問我,你寫的究竟是真實抑或虛構?我為了創作這本書,查閱了大量的檔案與資料,並且結交許多藏人朋友,與阿沛.阿旺晉美先生身邊的友人有著很深刻的接觸——當然我不便說出他們的身份。當時我思考該如何著筆此本創作,我也可以像寫歷史一樣,因手中握有許多相關資料。但是我覺得單憑歷史簡單的描繪,不足以表達藏人的苦難。我可以列舉在1959年藏人大起義中,有多少藏人犧性,西藏有多少的寺院被中共暴政摧毀,中共在寺廟裡安排了多少宗教特務;但這些數字在藏人的苦難面前顯得如此蒼白,所以我選擇用文學的筆觸來創作這本著作。
有人問我,這本書到底是怎樣的書?是小說還是詩歌,是詩還是哲學著作?我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本書的創作形式是由我對藏人心靈的體驗所決定的。有的人說這不是一本小說,因為它不是傳統的小說形式——就像編輯小姐寫的「開啟了全新的小說敘述」。藏人是一個充滿詩意的民族,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與低地人不同,他們沒有那麼多對物性、物質的慾望,但是他們有很多心靈的慾望,他們喝了酒就會笑得像一團火燄般。我記得有一位前世的達賴喇嘛就是一位詩人,他寫的詩那麼美。與其他宗教相比,藏傳佛教本身極為哲學化。透過對前世達賴喇嘛的詩之閱讀,我感覺到藏人既有一顆充滿哲理的心;又有一顆充滿詩意的心。
我於七次入藏、於藏人的交流當中,感覺到他們是最善良的民族,而這樣的民族卻身處於痛苦之中。小說裡寫了許多藏人具體的痛苦。我看過一本書,它僅從現象上去批評藏人如何落後、衣著不整等,當人們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藏人時,我覺得他們那骯髒、以物性為標準的心,根本無法解理一個把整個人生當作一次朝聖之旅的民族,他們的心中追求的是什麼!在現今生命普遍在物慾中腐爛的時代,藏人的這種情懷,是屬於整個人類的精神財富。
有的人說我是同情藏人,錯了!有的人說我是同情弱小的民族,更錯了!
不是我同情藏人,是我被藏人如此美麗的人格深深地感動!不感動我,我不會去寫,我感動得不足以形容,這震撼了我。我一定要讓藏人的苦難,透過我的筆,成為自由的史詩與生命的哲理,我可能才完成此生活著的一點意義。
另外,說到藏人是個弱小的民族,也許從現在人數上看藏人的確是少了些,但是藏人在歷史上是極其強悍的民族。吐蕃王國時代,藏人曾開啟強大的唐帝國的城門,迫使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女人——文成公主送至西藏和親。從前如此強大的民族,他們曾經像那鐵褐色山高原的風暴盤旋呼嘯,但他們信奉、皈依了佛教。在藏傳佛教中,風暴平息了,大海平靜了,藏族原本強悍的銳氣變成一個悲憫蒼生的宗教存在。這個宗教的存在到底有何意義和價值?我之所以認為藏傳佛教為人類保存了最後的精神價值,理由之一是祂創造出了當今世界上,最高貴聖潔美麗而又自由的族群,那就是藏人。走進西藏,當目光與藏族的少女對視時會驚覺,黑色,是世界上最燦爛的色彩。其人格是文化和文明的總結,也是藏人最主要的象徵。然而這樣的文化卻處於現實的危險之中。我有時覺得自己太沒有能力了!
我在書中最後寫到:「我沒有辦法幫藏人做更多的事情,我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讓那些在強權之下為了堅持自己精神的信念而死去的這些美麗高貴的男女,通過我的書能夠重新復活,獲得不朽的存在形式」。我只能做到如此。但我多麼希望能看到流亡的藏人能夠重返自己的故鄉,能夠重新在那片高原上展開自己神聖的心靈之旅。我不知道我能為藏人做什麼,有的人說我做了很多,但我只能用筆來寫這本書,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啊!
當整個世界尚處於黑暗之中時,西藏的雪山燃燒起第一道朝霞;當整個世界皆沉入夜色當中時,西藏高原的雪山仍閃耀著最後一抺晚霞。那是一個充滿猶如金色皇冠般雄偉壯麗的雪山土地。東亞大陸、南亞次大陸、東南亞等所有偉大的河流,都是發源自這片高原。它養育了印度與中華兩個偉大的文化。我們現在該做的,是要思索應如何回饋這片土地。我們為何會允許一個鐵血權力把如此聖潔的高地變成一個心靈的地獄?那些政治家、領袖、商人們,還有那些所謂的宗教領袖們,你們不感到恥辱嗎?
鑒於時間的關係就不多說了。我很感謝編輯把這段話摘出來,我唸一遍作為最後的結尾:「我走上這荒涼的高原是為了尋找美麗、真實、聖潔的生命。我找到了,但他們又離開了我……。索朗白牡、達娃、珠牡和貝吉多傑,他們都默默地消失了,他們的身影被鐵褐色荒原上那漫遊萬里的青銅色長風吹散了,但我要使他們消失於無邊荒涼中的美麗生命,成為流傳千古的詩;成為萬年不朽的歌;成為金色日球的高貴魂魄!」
謝謝大家。
答問:西藏文化在流亡中
曾建元:謝謝袁老師。他本來是一位法學的教授,但他則選擇以小說的形式來表達他對於西藏問題的看法。他剛剛的發言當中一再提到,我們該要如何去喚回我們對自由精神作為人的本質的一種力量,而他至少認為文學感性的形式,可以去感動人心,對於人之情感的謳歌所散發的力量,會比歷史學、法學或政治學的那種學術文字更來得大。
接下來還有一段時間,各位讀友可以跟袁教授進一步提問,大家可以就看了這本書,──還沒看過這本書也沒關係,有任何問題與想法自由表達,最後再請袁教授做綜合答覆。現在歡迎各位發言。
蘇明(民主中國陣線加拿大分部副主席):達瓦您好,文革時期,不光是西藏的文化、甚至整個中華文化都受到破壞。目前中國政府對西藏宗教有哪些有限制?
跋熱.達瓦才仁:剛剛你談到一個概念,很多人都會說文革時不僅僅是西藏,中國的文化也遭遇到破壞,其實這不是完全正確的。文化有新陳代謝,它有承載的問題。中國的文化都是用中文承載的,中國的共產主義也是一種文化。在五四運動中,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知識份子許多主張西化,這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它使部份的傳統文化自動消滅,但這一過程卻並非來自外來的壓迫。傳統的中華文化自動消滅的同時,也吸收了西方的東西,所以對中國來說,其實是消滅了一部份,吸收了一部份,它並沒有全部被消滅,或者說只是一種新陳代謝,汰舊換新,至於後來發現汰換的不太對,那是後知後覺,從一開始中國知識份子都要去擁抱西方的文化,並從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那是一種本民族菁英份子自己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一種外力消滅。但西藏卻恰恰相反,不存在任何的汰舊換新,完全是赤裸裸的文化滅絕,就如我剛剛所言,包括西藏民族的文字、符號等通通都沒有了,不被允許存在,同時卻被強迫去接觸和學習異民族的文字和文化,完全是暴力脅迫,與西藏民族的選擇不僅沒有任何的關係,而且是恰恰相反的,所以這兩個完全不是同一個問題,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現在西藏的宗教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樣的地方,就如剛剛所談的,西藏的宗教是一個哲學的宗教。一個西藏的僧人,就像噶瑪巴他必須要逃到國外去學習,並不是他出家了就是噶瑪巴。從西藏人的角度而言,他出家必須要掌握佛教的經典理論,而這些你必須要學習十幾年,最少也要幾年,而且這種學習都要進行相互的切磋辯論,所以佛教有一個概念就是佛法就像是對金子的磨鍊一樣,你可以用各種方式不斷地去驗證祂,因此佛教是最辯證的。辯證法以前我自己讀過,我拿去與佛教僧侶討論,發現這些在大學裡面被認為是很高深的東西,在佛法裡面其實是最基本的課程。這樣一個高深的內容必須要經過十幾年的學習,最少要學十幾年,一般都要二十幾年,而且這種學習是要在各教派之間互相進行辯論探討的。中共在西藏,對宗教的允許是屬於僅僅允許你求神拜佛的,允許你拜拜,中共把佛教貶為求神拜佛的民間信仰的層次,把僧人視為類似神漢、巫婆的角色;但在西藏人的角度,僧人的角色並非如此,他是傳播佛法的,是一個非常高尚、非常有學問的工作,他這種學習必須要經過十幾年的工夫,但這種條件和環境完全不存在,我所謂完全不存在,是指所有都沒有了,即是我所說的,西藏的法脈已不在西藏,在流亡中。
說到修持佛法,就有非常多的限制,比如說一個西藏人要出家,則受到名額的管制,中國共產黨規定一個寺院的編制人數,大的寺院是五百人,中的寺院是一百人。但所有的寺院幾乎都會超編,因為出家人很多,在這裡,你的出家人身分,並非取決於你是否信仰宗教、是否受戒、寺院是否願意接受你等宗教因素,而是取決於中共政府宗教局黨官是否認定你是一個出家人,或者是寺院裡有無缺額,比如說必須等有人還俗或有人往生了,你才可以補上。如果等不到這些而你自己去出家,共產黨隨時都可以抓你,並以詐騙罪來「依法」判你,因為你一旦出家就會接受到別人的供養,而當局可以認定你冒充宗教人士,欺騙信徒。所以,你的出家身分是由共產黨幹部決定的,他們不承認,你私自出家就可以判你有罪,也因此,迫使很多的僧人逃亡到國外。現在還有一個叫愛國主義教育,要求所有的出家人都必須要攻擊達賴喇嘛,但西藏的宗教確信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在西藏的轉世,是西藏的保護神,你如果攻擊了達賴喇嘛,你就不會是一個完整的僧人,根本再也談不上修行的問題;但若不攻擊的話,則連僧人都當不成,這就是西藏宗教界所面臨的問題。哪怕是只是接受戒律的傳承,這個傳承也是不完整的,因為你必須要攻擊自己的上師。一般的西藏人不充許信仰達賴喇嘛,但他不信仰中共指定的班禪喇嘛也是不行,你必須要信。所以在西藏,信仰似乎變成了中共官員手中的玩具,他要你信,你不信也得信,他不許你信,你信也不行。這就是西藏目前宗教的現狀。所以西藏現在其實沒有宗教,只有一種祈福禳災的神漢巫婆這種規模、這種層次的宗教活動,而沒有真正佛法的傳承。





Posted by rosaceae at 20:20
│報導與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