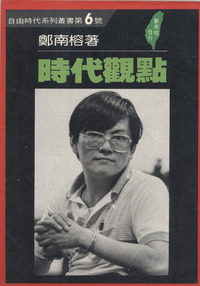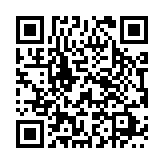2011年10月22日
必也正名乎!(2-1)--再覆達瓦才仁先生
台灣懸鉤子:這篇文章長達兩萬五千字,因此將分成五部分連載。
必也正名乎!再覆達瓦才仁先生,暨圖伯特正名的最後呼籲
/台灣懸鉤子、米那娃之梟
我想,我的部落格的常客應該都知道我與達瓦才仁先生在今年春夏對於正名的議題有所爭議,達瓦才仁先生五月中旬以一篇回覆作答於我,更在我的部落格留言板上侃侃而談,發表高見,我也找出當天座談會的錄音紀錄作成逐字稿,另外還將達瓦先生相關的文字一一陳現,務求其言無不盡,讓所有人再也 無誤解與偏聽之處。
這一段日子以來,我亦有幸得以查閱史料,思索議題,終於有了結論。對於我及米那娃之梟而言,目睹達瓦才仁先生形同「飲酖以求速死」的作法,卻還能振振有詞,百般狡辯,除了錯愕不置、瞠目結舌以外,也終於有了哀矜勿喜的心情。寫作這篇文章,我的用意絕非一逞口舌之快、也不是意氣用事,更與達瓦才仁先生個人無關,若不是因為他的主張已經屬於公領域的範疇,影響深遠,下文的檢視與批判才有其必要,而其目的著實希望求得真理水落石出,甚而突顯普世價值。而在此過程之中,若能對使用中文的博巴發揮震耳發聵之效能於萬一,那麼也就不辜負我這兩年來孜孜努力於譯事,對於圖伯特國家振興與其最終光復的一片深切期許與熱望。
本文分為兩大部分,歷史部分由我所撰寫;民主部分則由好友米那娃之梟主筆。
必也正名乎!再覆達瓦才仁先生,暨圖伯特正名的最後呼籲
/台灣懸鉤子、米那娃之梟
我想,我的部落格的常客應該都知道我與達瓦才仁先生在今年春夏對於正名的議題有所爭議,達瓦才仁先生五月中旬以一篇回覆作答於我,更在我的部落格留言板上侃侃而談,發表高見,我也找出當天座談會的錄音紀錄作成逐字稿,另外還將達瓦先生相關的文字一一陳現,務求其言無不盡,讓所有人再也 無誤解與偏聽之處。
這一段日子以來,我亦有幸得以查閱史料,思索議題,終於有了結論。對於我及米那娃之梟而言,目睹達瓦才仁先生形同「飲酖以求速死」的作法,卻還能振振有詞,百般狡辯,除了錯愕不置、瞠目結舌以外,也終於有了哀矜勿喜的心情。寫作這篇文章,我的用意絕非一逞口舌之快、也不是意氣用事,更與達瓦才仁先生個人無關,若不是因為他的主張已經屬於公領域的範疇,影響深遠,下文的檢視與批判才有其必要,而其目的著實希望求得真理水落石出,甚而突顯普世價值。而在此過程之中,若能對使用中文的博巴發揮震耳發聵之效能於萬一,那麼也就不辜負我這兩年來孜孜努力於譯事,對於圖伯特國家振興與其最終光復的一片深切期許與熱望。
本文分為兩大部分,歷史部分由我所撰寫;民主部分則由好友米那娃之梟主筆。
(1)歷史篇:自我想像難成真,胡亂解讀非歷史*
/台灣懸鉤子
*本文惠蒙印第安那大學艾略特‧史伯嶺教授(Professor Elliot Sperling)指正多端,受益良深,特此致謝。
達瓦先生「非用西藏不可」之主張,其最重要的根據乃是他的「明朝即有『西藏』說」。其主要證據為1575年的《明實錄》中所紀錄的廷議裏出現了此名詞。他並一口咬定,明朝之臣一定是因為1565年於日喀則建立有政權的藏巴汗,而藏巴王國是個獨立國家,從而衍生出「西藏」之名詞。他還舉出其他旁證:如明朝羅洪先《廣輿圖》、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以及清初張廷玉修撰的《明史》中的〈沐英傳〉等等。
然而,只要對他所提出的史料稍微考查,即可明白他上述的推論與說法完全無據,他對於史料之毫無調查、不求理解、甚而囫圇吞棗、不懂裝懂,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最可怕的是,他的詮釋甚而可能對於圖伯特是有害的。
任何一個歷史系的學生都知道考覈史實的重要,原因是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史書舛錯之處所在多有,除了作者無心之失,或手民之誤外,也有可能是後世在句讀時弄錯。因此史學入門的犖犖要者,乃是勾稽考查的基本工夫。因此,我也將一本此精神來一一檢視達瓦先生的證據。
蔡汝賢的「西藏」實為西海之訛寫:四個層次的解析
首先,我以四個層次抽絲剥繭證明達瓦先生所提出的主要證據乃為一字之訛。達瓦先生的主證,也就是兵科給事中蔡汝賢在1575年的奏言:
假如這位明朝大臣真的意指達瓦才仁先生所說的:「在七世達賴喇嘛之前,西藏政府的統治範圍是包括整個西藏三區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的「一個西藏」(1) ,那麼蔡汝賢的這個句子幾乎沒有辦法理解,因為蔡氏旋即又提到「南北諸番」,而「番」在這裏所指不是別的,正是明朝稱呼圖伯特之地區與民族的名號:「西番」之簡稱。假如真如達瓦先生所解釋的,明朝大臣之視野已經出現「一個西藏」,「所指包括西藏康區和安多地方」,又怎會有從南到北的眾多番族之說?
事實上,《明史‧西番諸衞傳》開宗明義:「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2) 明朝的另一位官員嚴從簡,在1574年所撰的《殊域周咨錄》也闡明:「吐蕃俗呼西蕃。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不只鄰近甘肅陝西的安多博巴被當時的中國人如此理解,就是圖伯特中部地區的衛藏兩區,明朝人也認為是諸國林立的局面,這一點從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時候,派宦官侯顯出使西域的記載亦可證明:「宣德二年二月〔1427年〕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斯藏、必力工瓦[懸鉤子按:今止貢]、靈藏[今鄧柯]、思達藏[今日喀則]諸國而還。」(3) 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左右,又有「西番諸國來貢,稱王號者百餘人」的記載 。(4) 達瓦先生想把「一個西藏」的概念強加於明朝大臣身上,班班可考的史籍無法證實此說,難以服人,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既然蔡汝賢的「西藏一路往來自由」絕對不可能指現代意義的「西藏」,那麼他所指究竟為何?如果我們在《明實錄》中尋求上下文,並對照其他信史中對同一件事的記錄,這裏的「西藏」應為「西海」之訛誤(西海是明朝對「青海湖」的稱謂)。比方說在蔡汝賢的奏言之前,《明實錄》萬曆三年四月的史料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提到了住在西海的俺答汗之子以建佛寺藉口,騷擾了當時四川邊境松潘一帶的博巴:
而短短四個月以後,《明實錄》又記載了俺答汗的姪孫、得利助手切盡黃台吉(6) 也為了蓋佛寺而與明朝溝通,應該與俺答汗之子所從事的是同一件事:
而此事的原委,《明史‧列傳‧西域二》有更清楚的說明:
其後續記載,還有《明實錄》萬曆五年三月:「前歲,俺荅丙兔乞建寺西海。朝廷不惜假以美名,助之以物料,正思化其悍暴,鼓其恭順耳。」 (8) 到了萬曆五年四月,又出現:「順義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額請,賜名仰乖。」(9) 因此,蔡氏奏言所說的「蓋許之建寺」,因其建寺地點就在西海之岸,那麼交通會因此通暢的,也應該是「西海一路」,其理甚明。
第三層,理解蔡氏整篇奏言的內容與發言動機,再溯及明朝中期邊防廷議的脈絡(context),蔡氏所意指更應是西海,殆無疑義。
明朝在十五、十六世紀常常遭受北方蒙古部族擾邊而備感憂患。在有明一朝,鄰近中國西北邊鎮的博巴各族,因為往往利用中國的「差發制」──每年固定用馬匹換取茶葉,因此被中國官員認為「頗柔服」,屬「熟番」也。所以,在中國守邊大臣的心目中,在河套蒙古擴張之際,「熟番」可作為中國的羽翼、屏障,或者以明朝人的話來說,「藩籬」是也。(10) 然而東蒙古之各部落擴張至西(青)海一帶,導致原本住在這裏的博巴不堪其擾而遷徙,未離開者,甚或反過頭來加入蒙古,兩者沆瀣一氣,共同危患中國,也不是不可引以為憂之事。(11) 因此嘉靖以後,就有頗多廷議是希望招撫青海一地的博巴各族,並仿效明初洪武永樂之例予以分封、授以官職,使他們心向中國,不受蒙古人脅從。(12)
隆慶年間(1567-1572年),明廷與蒙古的關係有了重大的突破。嘉靖年間(1522-1566年)曾率騎兵大肆侵擾中國邊鎮達五十次(13) 的蒙古萬戶領主俺答汗,其孫把漢那吉在此時因故叛投。當時明朝守邊大臣王崇古與方逢時,認為機不可失,決定接受其投誠,再利用他來招撫俺答。
然而北京的廷議仍然承繼嘉靖一朝的舊思維(14) ,多以為「虜情叵測」,此舉太過冒險。王、方兩位卻有極為有力的支持者,也就是當時內閣的宰輔張居正與高拱,他們力排眾議,高拱甚至把反對派的御史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促成與俺答汗的和議。終於在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明朝封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同意俺答汗曾經要求多年的貿易之請,在大同、宣府、延綏、寧夏等地開市通商。 (15)
此時的朝議或可區分為兩派,一派或可稱為「撫派」,另外一派為「勦派」,前者以王崇古與方逢時為代表,他們認為俺答等蒙古領袖並非不可理諭,只是因為無法與中國貿易而有搶掠之舉,只要明朝願意開市,就可以減少邊患(16) ,此派因為有張居正與高拱撐腰,又得皇帝之天聽,屬得勢者;後者則認為蒙古人天性狡詐,志在謀逆,因此必須「整搠邊備」以「挫其鋒」,使「少知斂戢耳」的守舊派,雖然目前勢弱,然而「任中敢言,彈劾勳戚而無顧忌」(17) 的兵科給事中蔡汝賢依然秉持異見,直上諫言無忌憚。
因此,在萬曆三年四月發出「賓兔蠶食諸番,撤我藩籬」議論的蔡氏,明顯承襲嘉靖時期以降的「藩籬」舊論,其發言動機與內容都是對於撫派的批評。他也一定清楚就在三個月前,總督三邊軍務的右都御史石茂華也曾老調重彈,專論明廷應該籠絡青海一地的博巴以抗蒙古:「套虜〔指河套蒙古〕盤聚西海、嘉峪關等處,聲勢甚重,納馬番族〔意指固定向中國進馬以換取茶葉的博巴〕與之並處,強弱不敵,萬一為所脅,構去我藩籬,貽害匪細。」(18) 因此,箇中的爭點自然是「西海一路」,不太可能會偏離明廷數十載以來念茲在茲的青海邊防要地,突然扯出風馬牛不相及的「西藏」,其理甚明。
第四層,達瓦才仁先生把蔡氏奏言中被訛寫的「西藏」一詞,與1565年奪權的藏巴王朝連結起起來,也就是說,在達瓦才仁先生的想像之中,在隆慶朝與萬曆初期,明廷就已經知道藏巴王朝的成立與存在。可是此說法卻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達瓦先生也未提出任何證據,只單憑自己的想像即作出如此斷言。
事實上,中國官修的正史中,《明實錄》找不到「藏巴汗」一詞,而清初所纂成的《明史》當中更付諸闕如,這三個字只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撰成的《清史稿》裏面。除了官修的正史外,明朝時曾任行人司行人(相當於今天的外交官)(19) 的嚴從簡在萬曆二年(1574年)所著的《殊域周咨錄》裏面,藏巴汗也未嘗見諸其專論〈西戎‧吐蕃〉之卷十一。嚴氏在序文中談到他撰輯此書的原則,乃在儘量採錄他所能看到的全部明朝文件,
因此,此書應很能代表當時明朝官員所能得到的外國資訊,更何況此書作成年代就在藏巴王朝成立之後,因此藏巴汗的資訊自然應該出現。然而,應有卻沒有,顯示的是明一朝在十六世紀時,對於烏斯藏的情況已漸感隔閡。其故安在?根據現代學者鄧銳齡在《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關係》之中的說法,自從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世宗拆毀番僧所居住的大慈恩寺後,明廷對於藏傳佛教的興趣低落,對烏斯藏所發生的事情一概不知,雙方聯繫中斷。(20) 而我們從所有可得的明朝史料中可以確切知道的是,藏巴王國的統治者從未有派遣貢使到明朝請求賜封,因為假如有的話,明廷根據傳統與慣例應該會賜給他們新的王號,而明朝歷史中從未有這樣的紀錄。
達瓦才仁先生提到唯一貌似證據的「證據」,是滿清尚未入主中原時的一件事,確實,滿清統治者皇太極在1637年左右送邀請函給達賴喇嘛之同時,也寫了信給藏巴汗,請他允許達賴喇嘛前往盛京 。(21)然而此一事件無法推論明廷的情況,也無法推導出明朝大臣「視野中已經出現了『西藏』」的結論。(另外,清朝也不是從皇太極開始稱呼「西藏」的,滿清至少一直到順治時都還稱藏巴汗為「圖白忒部落藏巴汗」 。(22) 達瓦才仁先生提到學者陳慶英的「西藏」起源之推測,事實上,陳氏所引述的清實錄文獻,其年代乃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23) ,達瓦才仁先生說此事可以「反證」皇太極時候的事情,還可以推導出康熙朝所造的「西藏」一詞源起於藏巴王朝,然而圖伯特中部的政治情勢早已丕變,此時拉藏汗擁立了一位假的達賴喇嘛並請康熙承認(24) ,難道是康熙心中還依然掛記著已逝的藏巴王朝,並以藏巴王朝來作為稱呼此地的符號?如此揣測太過天馬行空,沒有實據,難以成立。)因此達瓦才仁先生所謂「西藏」一詞是從藏巴王朝衍生的論斷是很有問題的。
(待續)
註釋:
(1) 跋熱‧達瓦才仁,《血祭雪域:西藏護教救國抗戰史》,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2003,第3頁。達瓦才仁先生又在〈回覆台灣懸鉤子的公開信〉中表示:「不論何時,『西藏』從來都沒有用來指Gstang地方。同樣,不論何時,『西藏』一詞都能夠實現『民族和地域』的雙重功能。」既然是斬釘截鐵的「不論何時」,我自然只能推論,達瓦先生的「一個統一的國家」之「一個西藏」概念一定也適用於明朝。
(2) 本文所引用的《明史》及《明實錄》內容,乃是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之免費「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查閱而得,特此申明並致謝忱。
《明史》卷三百三十,列傳第二百十八/西域二/西番諸衞 西寧 河州 洮州 岷州等番族諸衞(P.8539)。又見:《明史‧志》第六十六/兵二/衞所:「西番即古吐蕃。」
(3) 《明史》卷三百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鄭和 侯顯(P.7766)
(4) 《明史》卷一百九十九,列傳第八十七/王憲(P.5257)
(5) 由《明神宗實錄》卷三十二‧萬曆二年十二月(P.747)的記載「俺答二子賓兔,一住松山,一住西海」來推論,當時的朝廷似乎不區別俺答二子之名。然若以清初作成之《明史‧列傳‧西域二》:「時北部俺答猖獗,歲掠宣、大諸鎮。又羨青海富饒,三十八年攜子賓兔、丙兔等數萬眾,襲據其地。‧‧‧留賓兔據松山,丙兔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觀之,此處應作丙兔。
(6) 「切盡黃台吉」正名應為「庫圖克徹辰洪台吉」(生卒:1540年-1586年),是俺達汗的從孫(兄弟的孫子),也是他的得利助手。見郝繼忠,〈庫圖克徹辰洪台吉事略〉。
(7) 《明神宗實錄》:卷四十一,萬曆三年八月(P.929)。
(8) 《明神宗實錄》:卷六十,萬曆五年三月(P.1365)。
(9) 《明神宗實錄》:卷六十一,萬曆五年四月(P.1381)。此處「仰乖」應為「仰華」之訛。
(10) 《明史》卷三百三十,列傳第二百十八/西域二/西番諸衞:「時為陝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青海土最沃,且有番人屏蔽,故患猶不甚劇。」
(11) 同前引書:「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剌、阿爾禿厮獲罪其主,擁眾西奔。瞰知青海饒富,襲而據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遠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為所役屬。」又有:「自青海為寇所據,番不堪剽奪,私饋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饋曰添巴,或反為嚮導,交通無忌。而中國市馬亦鮮至,蓋已失捍外衞內之初意矣。」
(12) 同前引書:「〔嘉靖〕十一年,甘肅巡撫趙載等言:『亦不剌據海上已二十餘年,其黨卜兒孩獨傾心向化,求帖木哥等屬番來納款。宜因而撫之,或俾之納馬,或令其遣質,或授官給印,建立衞所,為我藩籬,於計為便。』」
(13) 全太錦,〈明蒙隆慶和議前後邊疆社會的變遷──以大同和豐州灘之間碰撞交流為中心〉,他從《明實錄》統計出俺答汗在嘉靖年間較大規模舉兵南搶中國北部邊鎮就有五十次。而小規模者更是不計其數。
(14) 嘉靖二十七年,俺答汗有意與明朝議和並與之貿易,孰料嘉靖皇帝卻答:「逆虜連歲寇邊,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各邊嚴兵禦防,如有執異,處以極典。」見前引書。
(15) 見「互動百科」「高拱」條。
(16) 方逢時,〈虜酋勢刼熟番疏〉,收錄於《皇明經世文編》卷三百二十,方氏在疏中表示他同意俺答之言,認為丙兔所以搶掠松潘之博巴,不過是因為無法在河西貢市。此疏乃是對蔡汝賢的反駁。而方逢時的意見當時被明神宗採納。方逢時另作〈與內閣兵部論邊情書〉,收於《大隱樓集》卷十二,乃是他向兵部解釋俺答汗求番文佛經、番僧等舉的用意。
(17) 《掖垣人鑒》卷十五,引自湯開健,〈中國現存最早的歐洲人形象資料 ──《東夷圖像》〉。
(18) 《明神宗實錄》卷三十四 萬曆三年正月(P.783)。
(19) 「行人司」乃由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所創,屬員負有「撫諭諸蕃」任務,約略等同於現今的外交官員。見《明史》志 凡七十五卷/卷七十四 志第五十/職官三/行人司(P.1809)。嚴氏在序文裏面提到他作此書之初衷,是因為他過去在行人司裏面作備員,雖未有被派遣到外國去的榮幸,卻不敢忘記全面瞭解各國的志願:「曩予備員行人,竊祿明時,每懷靡及,雖未嘗蒙殊域之遣,而不敢忘周咨之志。」
(20) 鄧銳齡,《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係》(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頁85。
(21) 巴黎高等社科院Anne-Marie Blondeau等,《遮蔽的圖伯特》(台北:前衛,2011),頁37。
(22) 陳慶英,〈漢文「西藏」一詞的來歷簡說〉,《陳慶英藏學論文集》下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頁1009。
(23) 前引書,頁1013。
(24) 巴黎高等社科院Anne-Marie Blondeau等,《遮蔽的圖伯特》(台北:前衛,2011),頁43。
附錄:(標點符號為我所加)
73史/編年/明實錄/神宗/卷三十七 萬曆三年四月(P.855)
俺答子賓兔住牧西海,役屬作兒革、白利等諸番。隨令寄信松 潘番、漢,以迎佛盖寺為名,屢傳釁息。四川撫臣曾者吾、按臣郭 莊以聞,謂:宜速行陝西總督,諭令順義王俺答嚴戢賓兔,無得 垂涎邊境、自敗盟好。于是兵科都給事中蔡汝賢奏言:賓兔蠶 食諸番,撤我籓籬,逆志固已萌矣。議者不察,猶欲傳諭俺答,鈐 制賓兔。夫奄奄病酋,墓木已拱,安能繫諸酋之手足耶?且賓兔 前搶西寧,已行戒諭,曾莫之忌,可見于前事矣。乞勑該部亟咨 該鎮,勘破虜情,整搠邊備,或先事以伐其謀,或遣諜以擕其黨, 或增兵以扼其隘,或相机以挫其鋒。令犯順者創,脅從者解,狂 虜聞之,少知歛戢耳。且虜自稱貢以來,所要我者屢變,索鍋而與之鍋,求市而與之市,增馬而與之增,將來邊計安知底止?乃 若己蜀之釁,又自焚修之說啟也,盖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 來自繇,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彼黠虜豈真有 豈真有校:影印本豈字不清楚。從善 之念哉,其挾詐用術,遠交近攻,不獨賓兔為然明矣 不獨賓兔為然明矣校:廣本然下有也彰彰三字。惟 天語 叮嚀當事諸臣,毋蹈往轍,克勵新圖,無苟取一時之安,重貽他 日之悔。章下兵部
/台灣懸鉤子
*本文惠蒙印第安那大學艾略特‧史伯嶺教授(Professor Elliot Sperling)指正多端,受益良深,特此致謝。
達瓦先生「非用西藏不可」之主張,其最重要的根據乃是他的「明朝即有『西藏』說」。其主要證據為1575年的《明實錄》中所紀錄的廷議裏出現了此名詞。他並一口咬定,明朝之臣一定是因為1565年於日喀則建立有政權的藏巴汗,而藏巴王國是個獨立國家,從而衍生出「西藏」之名詞。他還舉出其他旁證:如明朝羅洪先《廣輿圖》、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以及清初張廷玉修撰的《明史》中的〈沐英傳〉等等。
然而,只要對他所提出的史料稍微考查,即可明白他上述的推論與說法完全無據,他對於史料之毫無調查、不求理解、甚而囫圇吞棗、不懂裝懂,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最可怕的是,他的詮釋甚而可能對於圖伯特是有害的。
任何一個歷史系的學生都知道考覈史實的重要,原因是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史書舛錯之處所在多有,除了作者無心之失,或手民之誤外,也有可能是後世在句讀時弄錯。因此史學入門的犖犖要者,乃是勾稽考查的基本工夫。因此,我也將一本此精神來一一檢視達瓦先生的證據。
蔡汝賢的「西藏」實為西海之訛寫:四個層次的解析
首先,我以四個層次抽絲剥繭證明達瓦先生所提出的主要證據乃為一字之訛。達瓦先生的主證,也就是兵科給事中蔡汝賢在1575年的奏言:
「蓋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全文請見附錄)
假如這位明朝大臣真的意指達瓦才仁先生所說的:「在七世達賴喇嘛之前,西藏政府的統治範圍是包括整個西藏三區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的「一個西藏」(1) ,那麼蔡汝賢的這個句子幾乎沒有辦法理解,因為蔡氏旋即又提到「南北諸番」,而「番」在這裏所指不是別的,正是明朝稱呼圖伯特之地區與民族的名號:「西番」之簡稱。假如真如達瓦先生所解釋的,明朝大臣之視野已經出現「一個西藏」,「所指包括西藏康區和安多地方」,又怎會有從南到北的眾多番族之說?
事實上,《明史‧西番諸衞傳》開宗明義:「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2) 明朝的另一位官員嚴從簡,在1574年所撰的《殊域周咨錄》也闡明:「吐蕃俗呼西蕃。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不只鄰近甘肅陝西的安多博巴被當時的中國人如此理解,就是圖伯特中部地區的衛藏兩區,明朝人也認為是諸國林立的局面,這一點從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時候,派宦官侯顯出使西域的記載亦可證明:「宣德二年二月〔1427年〕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斯藏、必力工瓦[懸鉤子按:今止貢]、靈藏[今鄧柯]、思達藏[今日喀則]諸國而還。」(3) 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左右,又有「西番諸國來貢,稱王號者百餘人」的記載 。(4) 達瓦先生想把「一個西藏」的概念強加於明朝大臣身上,班班可考的史籍無法證實此說,難以服人,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既然蔡汝賢的「西藏一路往來自由」絕對不可能指現代意義的「西藏」,那麼他所指究竟為何?如果我們在《明實錄》中尋求上下文,並對照其他信史中對同一件事的記錄,這裏的「西藏」應為「西海」之訛誤(西海是明朝對「青海湖」的稱謂)。比方說在蔡汝賢的奏言之前,《明實錄》萬曆三年四月的史料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提到了住在西海的俺答汗之子以建佛寺藉口,騷擾了當時四川邊境松潘一帶的博巴:
「俺答子賓兔[應為丙兔之誤(5) ]住牧西海,役屬作兒革、白利等諸番。隨令寄信松潘番、漢,以迎佛蓋寺為名,屢傳釁息[釁息,爭端也]。四川撫臣曾省吾、按臣郭莊以聞。謂:『宜速行陝西總督諭令順義王俺答,嚴戢賓兔,無得垂涎邊境,自敗盟好。』」
而短短四個月以後,《明實錄》又記載了俺答汗的姪孫、得利助手切盡黃台吉(6) 也為了蓋佛寺而與明朝溝通,應該與俺答汗之子所從事的是同一件事:
「先是,虜酋切盡黃台吉等乞于西海地方及嘉谷関外盖寺焚修[焚香修道也],事下。川陝三省督撫勘議。禮部覆議:各虜已採木興工,而責其改造于五王城,勢既不能,不若因而許之,以鼓其修善,而杜其嘉谷関外之請。蓋中國之禦夷,惟在邊関之有備,而擄之順逆,又不在一寺之遠近也。」(7)
而此事的原委,《明史‧列傳‧西域二》有更清楚的說明:
「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為名,請建寺青海及嘉峪關外,為久居計。廷臣多言不可許,禮官言:『彼已採木興工,而令改建於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況中國之禦戎,惟在邊關之有備。戎之順逆,亦不在一寺之遠近。』帝許之。丙兔既得請,又近脅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懼逼,乞令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
其後續記載,還有《明實錄》萬曆五年三月:「前歲,俺荅丙兔乞建寺西海。朝廷不惜假以美名,助之以物料,正思化其悍暴,鼓其恭順耳。」 (8) 到了萬曆五年四月,又出現:「順義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額請,賜名仰乖。」(9) 因此,蔡氏奏言所說的「蓋許之建寺」,因其建寺地點就在西海之岸,那麼交通會因此通暢的,也應該是「西海一路」,其理甚明。
第三層,理解蔡氏整篇奏言的內容與發言動機,再溯及明朝中期邊防廷議的脈絡(context),蔡氏所意指更應是西海,殆無疑義。
明朝在十五、十六世紀常常遭受北方蒙古部族擾邊而備感憂患。在有明一朝,鄰近中國西北邊鎮的博巴各族,因為往往利用中國的「差發制」──每年固定用馬匹換取茶葉,因此被中國官員認為「頗柔服」,屬「熟番」也。所以,在中國守邊大臣的心目中,在河套蒙古擴張之際,「熟番」可作為中國的羽翼、屏障,或者以明朝人的話來說,「藩籬」是也。(10) 然而東蒙古之各部落擴張至西(青)海一帶,導致原本住在這裏的博巴不堪其擾而遷徙,未離開者,甚或反過頭來加入蒙古,兩者沆瀣一氣,共同危患中國,也不是不可引以為憂之事。(11) 因此嘉靖以後,就有頗多廷議是希望招撫青海一地的博巴各族,並仿效明初洪武永樂之例予以分封、授以官職,使他們心向中國,不受蒙古人脅從。(12)
隆慶年間(1567-1572年),明廷與蒙古的關係有了重大的突破。嘉靖年間(1522-1566年)曾率騎兵大肆侵擾中國邊鎮達五十次(13) 的蒙古萬戶領主俺答汗,其孫把漢那吉在此時因故叛投。當時明朝守邊大臣王崇古與方逢時,認為機不可失,決定接受其投誠,再利用他來招撫俺答。
然而北京的廷議仍然承繼嘉靖一朝的舊思維(14) ,多以為「虜情叵測」,此舉太過冒險。王、方兩位卻有極為有力的支持者,也就是當時內閣的宰輔張居正與高拱,他們力排眾議,高拱甚至把反對派的御史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促成與俺答汗的和議。終於在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明朝封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同意俺答汗曾經要求多年的貿易之請,在大同、宣府、延綏、寧夏等地開市通商。 (15)
此時的朝議或可區分為兩派,一派或可稱為「撫派」,另外一派為「勦派」,前者以王崇古與方逢時為代表,他們認為俺答等蒙古領袖並非不可理諭,只是因為無法與中國貿易而有搶掠之舉,只要明朝願意開市,就可以減少邊患(16) ,此派因為有張居正與高拱撐腰,又得皇帝之天聽,屬得勢者;後者則認為蒙古人天性狡詐,志在謀逆,因此必須「整搠邊備」以「挫其鋒」,使「少知斂戢耳」的守舊派,雖然目前勢弱,然而「任中敢言,彈劾勳戚而無顧忌」(17) 的兵科給事中蔡汝賢依然秉持異見,直上諫言無忌憚。
因此,在萬曆三年四月發出「賓兔蠶食諸番,撤我藩籬」議論的蔡氏,明顯承襲嘉靖時期以降的「藩籬」舊論,其發言動機與內容都是對於撫派的批評。他也一定清楚就在三個月前,總督三邊軍務的右都御史石茂華也曾老調重彈,專論明廷應該籠絡青海一地的博巴以抗蒙古:「套虜〔指河套蒙古〕盤聚西海、嘉峪關等處,聲勢甚重,納馬番族〔意指固定向中國進馬以換取茶葉的博巴〕與之並處,強弱不敵,萬一為所脅,構去我藩籬,貽害匪細。」(18) 因此,箇中的爭點自然是「西海一路」,不太可能會偏離明廷數十載以來念茲在茲的青海邊防要地,突然扯出風馬牛不相及的「西藏」,其理甚明。
第四層,達瓦才仁先生把蔡氏奏言中被訛寫的「西藏」一詞,與1565年奪權的藏巴王朝連結起起來,也就是說,在達瓦才仁先生的想像之中,在隆慶朝與萬曆初期,明廷就已經知道藏巴王朝的成立與存在。可是此說法卻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達瓦先生也未提出任何證據,只單憑自己的想像即作出如此斷言。
事實上,中國官修的正史中,《明實錄》找不到「藏巴汗」一詞,而清初所纂成的《明史》當中更付諸闕如,這三個字只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撰成的《清史稿》裏面。除了官修的正史外,明朝時曾任行人司行人(相當於今天的外交官)(19) 的嚴從簡在萬曆二年(1574年)所著的《殊域周咨錄》裏面,藏巴汗也未嘗見諸其專論〈西戎‧吐蕃〉之卷十一。嚴氏在序文中談到他撰輯此書的原則,乃在儘量採錄他所能看到的全部明朝文件,
「若我朝之撫馭各夷者,其文典藏諸私館,世莫易窺,有苟見於各帙者,必盡著之,只懼其語焉不詳,未論其擇焉不精也。」
因此,此書應很能代表當時明朝官員所能得到的外國資訊,更何況此書作成年代就在藏巴王朝成立之後,因此藏巴汗的資訊自然應該出現。然而,應有卻沒有,顯示的是明一朝在十六世紀時,對於烏斯藏的情況已漸感隔閡。其故安在?根據現代學者鄧銳齡在《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關係》之中的說法,自從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世宗拆毀番僧所居住的大慈恩寺後,明廷對於藏傳佛教的興趣低落,對烏斯藏所發生的事情一概不知,雙方聯繫中斷。(20) 而我們從所有可得的明朝史料中可以確切知道的是,藏巴王國的統治者從未有派遣貢使到明朝請求賜封,因為假如有的話,明廷根據傳統與慣例應該會賜給他們新的王號,而明朝歷史中從未有這樣的紀錄。
達瓦才仁先生提到唯一貌似證據的「證據」,是滿清尚未入主中原時的一件事,確實,滿清統治者皇太極在1637年左右送邀請函給達賴喇嘛之同時,也寫了信給藏巴汗,請他允許達賴喇嘛前往盛京 。(21)然而此一事件無法推論明廷的情況,也無法推導出明朝大臣「視野中已經出現了『西藏』」的結論。(另外,清朝也不是從皇太極開始稱呼「西藏」的,滿清至少一直到順治時都還稱藏巴汗為「圖白忒部落藏巴汗」 。(22) 達瓦才仁先生提到學者陳慶英的「西藏」起源之推測,事實上,陳氏所引述的清實錄文獻,其年代乃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23) ,達瓦才仁先生說此事可以「反證」皇太極時候的事情,還可以推導出康熙朝所造的「西藏」一詞源起於藏巴王朝,然而圖伯特中部的政治情勢早已丕變,此時拉藏汗擁立了一位假的達賴喇嘛並請康熙承認(24) ,難道是康熙心中還依然掛記著已逝的藏巴王朝,並以藏巴王朝來作為稱呼此地的符號?如此揣測太過天馬行空,沒有實據,難以成立。)因此達瓦才仁先生所謂「西藏」一詞是從藏巴王朝衍生的論斷是很有問題的。
(待續)
註釋:
(1) 跋熱‧達瓦才仁,《血祭雪域:西藏護教救國抗戰史》,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2003,第3頁。達瓦才仁先生又在〈回覆台灣懸鉤子的公開信〉中表示:「不論何時,『西藏』從來都沒有用來指Gstang地方。同樣,不論何時,『西藏』一詞都能夠實現『民族和地域』的雙重功能。」既然是斬釘截鐵的「不論何時」,我自然只能推論,達瓦先生的「一個統一的國家」之「一個西藏」概念一定也適用於明朝。
(2) 本文所引用的《明史》及《明實錄》內容,乃是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之免費「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查閱而得,特此申明並致謝忱。
《明史》卷三百三十,列傳第二百十八/西域二/西番諸衞 西寧 河州 洮州 岷州等番族諸衞(P.8539)。又見:《明史‧志》第六十六/兵二/衞所:「西番即古吐蕃。」
(3) 《明史》卷三百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鄭和 侯顯(P.7766)
(4) 《明史》卷一百九十九,列傳第八十七/王憲(P.5257)
(5) 由《明神宗實錄》卷三十二‧萬曆二年十二月(P.747)的記載「俺答二子賓兔,一住松山,一住西海」來推論,當時的朝廷似乎不區別俺答二子之名。然若以清初作成之《明史‧列傳‧西域二》:「時北部俺答猖獗,歲掠宣、大諸鎮。又羨青海富饒,三十八年攜子賓兔、丙兔等數萬眾,襲據其地。‧‧‧留賓兔據松山,丙兔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觀之,此處應作丙兔。
(6) 「切盡黃台吉」正名應為「庫圖克徹辰洪台吉」(生卒:1540年-1586年),是俺達汗的從孫(兄弟的孫子),也是他的得利助手。見郝繼忠,〈庫圖克徹辰洪台吉事略〉。
(7) 《明神宗實錄》:卷四十一,萬曆三年八月(P.929)。
(8) 《明神宗實錄》:卷六十,萬曆五年三月(P.1365)。
(9) 《明神宗實錄》:卷六十一,萬曆五年四月(P.1381)。此處「仰乖」應為「仰華」之訛。
(10) 《明史》卷三百三十,列傳第二百十八/西域二/西番諸衞:「時為陝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青海土最沃,且有番人屏蔽,故患猶不甚劇。」
(11) 同前引書:「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剌、阿爾禿厮獲罪其主,擁眾西奔。瞰知青海饒富,襲而據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遠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為所役屬。」又有:「自青海為寇所據,番不堪剽奪,私饋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饋曰添巴,或反為嚮導,交通無忌。而中國市馬亦鮮至,蓋已失捍外衞內之初意矣。」
(12) 同前引書:「〔嘉靖〕十一年,甘肅巡撫趙載等言:『亦不剌據海上已二十餘年,其黨卜兒孩獨傾心向化,求帖木哥等屬番來納款。宜因而撫之,或俾之納馬,或令其遣質,或授官給印,建立衞所,為我藩籬,於計為便。』」
(13) 全太錦,〈明蒙隆慶和議前後邊疆社會的變遷──以大同和豐州灘之間碰撞交流為中心〉,他從《明實錄》統計出俺答汗在嘉靖年間較大規模舉兵南搶中國北部邊鎮就有五十次。而小規模者更是不計其數。
(14) 嘉靖二十七年,俺答汗有意與明朝議和並與之貿易,孰料嘉靖皇帝卻答:「逆虜連歲寇邊,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各邊嚴兵禦防,如有執異,處以極典。」見前引書。
(15) 見「互動百科」「高拱」條。
(16) 方逢時,〈虜酋勢刼熟番疏〉,收錄於《皇明經世文編》卷三百二十,方氏在疏中表示他同意俺答之言,認為丙兔所以搶掠松潘之博巴,不過是因為無法在河西貢市。此疏乃是對蔡汝賢的反駁。而方逢時的意見當時被明神宗採納。方逢時另作〈與內閣兵部論邊情書〉,收於《大隱樓集》卷十二,乃是他向兵部解釋俺答汗求番文佛經、番僧等舉的用意。
(17) 《掖垣人鑒》卷十五,引自湯開健,〈中國現存最早的歐洲人形象資料 ──《東夷圖像》〉。
(18) 《明神宗實錄》卷三十四 萬曆三年正月(P.783)。
(19) 「行人司」乃由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所創,屬員負有「撫諭諸蕃」任務,約略等同於現今的外交官員。見《明史》志 凡七十五卷/卷七十四 志第五十/職官三/行人司(P.1809)。嚴氏在序文裏面提到他作此書之初衷,是因為他過去在行人司裏面作備員,雖未有被派遣到外國去的榮幸,卻不敢忘記全面瞭解各國的志願:「曩予備員行人,竊祿明時,每懷靡及,雖未嘗蒙殊域之遣,而不敢忘周咨之志。」
(20) 鄧銳齡,《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係》(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頁85。
(21) 巴黎高等社科院Anne-Marie Blondeau等,《遮蔽的圖伯特》(台北:前衛,2011),頁37。
(22) 陳慶英,〈漢文「西藏」一詞的來歷簡說〉,《陳慶英藏學論文集》下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頁1009。
(23) 前引書,頁1013。
(24) 巴黎高等社科院Anne-Marie Blondeau等,《遮蔽的圖伯特》(台北:前衛,2011),頁43。
附錄:(標點符號為我所加)
73史/編年/明實錄/神宗/卷三十七 萬曆三年四月(P.855)
俺答子賓兔住牧西海,役屬作兒革、白利等諸番。隨令寄信松 潘番、漢,以迎佛盖寺為名,屢傳釁息。四川撫臣曾者吾、按臣郭 莊以聞,謂:宜速行陝西總督,諭令順義王俺答嚴戢賓兔,無得 垂涎邊境、自敗盟好。于是兵科都給事中蔡汝賢奏言:賓兔蠶 食諸番,撤我籓籬,逆志固已萌矣。議者不察,猶欲傳諭俺答,鈐 制賓兔。夫奄奄病酋,墓木已拱,安能繫諸酋之手足耶?且賓兔 前搶西寧,已行戒諭,曾莫之忌,可見于前事矣。乞勑該部亟咨 該鎮,勘破虜情,整搠邊備,或先事以伐其謀,或遣諜以擕其黨, 或增兵以扼其隘,或相机以挫其鋒。令犯順者創,脅從者解,狂 虜聞之,少知歛戢耳。且虜自稱貢以來,所要我者屢變,索鍋而與之鍋,求市而與之市,增馬而與之增,將來邊計安知底止?乃 若己蜀之釁,又自焚修之說啟也,盖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 來自繇,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彼黠虜豈真有 豈真有校:影印本豈字不清楚。從善 之念哉,其挾詐用術,遠交近攻,不獨賓兔為然明矣 不獨賓兔為然明矣校:廣本然下有也彰彰三字。惟 天語 叮嚀當事諸臣,毋蹈往轍,克勵新圖,無苟取一時之安,重貽他 日之悔。章下兵部
Posted by rosaceae at 23:46│Comments(4)
│必也正名乎
留言
台灣懸鉤子、米那娃之梟:
非常感激你們為真理而寫,正義而呼,面對真實一切的狡辯多麼的不堪。我對達瓦一向敬重,但大是大非面前我仍有自己的堅持。90年代以來達瓦把自我定位Tibet相關中文的百科全書,無所不知。今天到台灣繼續賣弄自己天馬行空的歷史觀,就要面對挑戰與檢驗,不能只憑自我感覺良好。
我一直覺得達瓦對中國的歷史有誤讀,誤讀有三個原因,第一:個人的中文程度。第二:所讀的歷史書本身。第三:時空環境。
第一,個人的中文程度有限,達瓦是警校專科生。(嚴格意義上高中沒畢業,再加上中國西北五省的教育非常落後,再者中文不是他的母語)之後的社會歷練也不夠,他並不再任何學術機構任職,充其量只能說他個人的愛好,揣摸著讀一些三國演義之類的書籍。第二:他所接觸的歷史書本幾乎是國共篡改的白話編譯文,若不是白話文,對文言文的原意有很大的誤讀。即便是中國歷史學者都承認當代中國歷史權威人士在海外,不在中國。因為魯迅把文言文定位死文字之後,很少人有興趣去讀文言文。第三時空環境的不同,老將失去中國大地,流亡台灣,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跟歷代的中國皇帝一樣用文化來維繫自己的正統,所以台灣的課本中文言文佔有很大的比例。相反中共為了革命革了中國文化的命,所以這樣的情境下達瓦所知的中國古文是非常有限的,除非他有特異功能。
非常感激你們為真理而寫,正義而呼,面對真實一切的狡辯多麼的不堪。我對達瓦一向敬重,但大是大非面前我仍有自己的堅持。90年代以來達瓦把自我定位Tibet相關中文的百科全書,無所不知。今天到台灣繼續賣弄自己天馬行空的歷史觀,就要面對挑戰與檢驗,不能只憑自我感覺良好。
我一直覺得達瓦對中國的歷史有誤讀,誤讀有三個原因,第一:個人的中文程度。第二:所讀的歷史書本身。第三:時空環境。
第一,個人的中文程度有限,達瓦是警校專科生。(嚴格意義上高中沒畢業,再加上中國西北五省的教育非常落後,再者中文不是他的母語)之後的社會歷練也不夠,他並不再任何學術機構任職,充其量只能說他個人的愛好,揣摸著讀一些三國演義之類的書籍。第二:他所接觸的歷史書本幾乎是國共篡改的白話編譯文,若不是白話文,對文言文的原意有很大的誤讀。即便是中國歷史學者都承認當代中國歷史權威人士在海外,不在中國。因為魯迅把文言文定位死文字之後,很少人有興趣去讀文言文。第三時空環境的不同,老將失去中國大地,流亡台灣,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跟歷代的中國皇帝一樣用文化來維繫自己的正統,所以台灣的課本中文言文佔有很大的比例。相反中共為了革命革了中國文化的命,所以這樣的情境下達瓦所知的中國古文是非常有限的,除非他有特異功能。
Posted by 美西安多瓦 at 2011年10月25日 03:01
台灣懸鉤子:
昨天我寫了較長的留言,至今沒有刊載,不知何故?多年前我前往已故的台灣歷史學家及作家柏楊在台北新店花園新城的家,專門請教有關中國與吐蕃特歷史上的問題。他給我說“中國基本上沒有國史,有的是家史,但這個家史也是偽造多數,篡改歷史是中國歷朝歷代的重要使命。所以研究同代的歷史必須從上代或上上代開始。”所以我合理的推斷達瓦所讀的歷史書大概都是民國初年或中共執政後的書籍。其二:我也懷疑達瓦對中國古文的理解能力,在紅旗下長大的中國文人大部分對古文了解有限,更何況對達瓦來說難上加難(我沒有貶低的意思,時空環境不同所造成的)。
我非常敬佩台灣懸鉤子鍥而不捨的考究精神,讓我們族人中有些人目中無人,口若懸河,自我感覺良好者是一個很好警訊。
昨天我寫了較長的留言,至今沒有刊載,不知何故?多年前我前往已故的台灣歷史學家及作家柏楊在台北新店花園新城的家,專門請教有關中國與吐蕃特歷史上的問題。他給我說“中國基本上沒有國史,有的是家史,但這個家史也是偽造多數,篡改歷史是中國歷朝歷代的重要使命。所以研究同代的歷史必須從上代或上上代開始。”所以我合理的推斷達瓦所讀的歷史書大概都是民國初年或中共執政後的書籍。其二:我也懷疑達瓦對中國古文的理解能力,在紅旗下長大的中國文人大部分對古文了解有限,更何況對達瓦來說難上加難(我沒有貶低的意思,時空環境不同所造成的)。
我非常敬佩台灣懸鉤子鍥而不捨的考究精神,讓我們族人中有些人目中無人,口若懸河,自我感覺良好者是一個很好警訊。
Posted by 美西安多瓦 at 2011年10月30日 04:51
感謝美西安多瓦的聲援。
Posted by rosaceae at 2011年10月30日 19:12
at 2011年10月30日 19:12
 at 2011年10月30日 19:12
at 2011年10月30日 19:12美西安多瓦:
你好?你在留言中写道:“專門請教有關中國與吐蕃特歷史上的問題。”
“吐蕃”称呼,早在六十多年前,就被台湾政府命令废止。请看:
蕃(番)族研究
歡迎光臨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10月25日 我國抗日戰爭勝利,台澎光復受降,正式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台北市;10月26日宣布台灣為中華民國一行省;31日行政長官公署設置台灣省 ... 12月13日 行政長官公署代電:本省高山族同胞居住高山地帶者計15-16萬人,過去土蕃、蕃族、蠻族等歧視名詞,一律不再使用。
基督教長老會的傳入對排灣族傳統婚禮的影響 蔡南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台灣原住民,究竟何時、 ... 兩大類,一為「生蕃」(又稱高山蕃、蕃人、兇蕃、蕃、蕃民、野蕃、界外蕃及蕃族等);另一為「熟蕃」(又稱平地蕃、土蕃、歸化生蕃、良蕃、社蕃、歸化蕃、流蕃、平蕃。
你好?你在留言中写道:“專門請教有關中國與吐蕃特歷史上的問題。”
“吐蕃”称呼,早在六十多年前,就被台湾政府命令废止。请看:
蕃(番)族研究
歡迎光臨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10月25日 我國抗日戰爭勝利,台澎光復受降,正式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台北市;10月26日宣布台灣為中華民國一行省;31日行政長官公署設置台灣省 ... 12月13日 行政長官公署代電:本省高山族同胞居住高山地帶者計15-16萬人,過去土蕃、蕃族、蠻族等歧視名詞,一律不再使用。
基督教長老會的傳入對排灣族傳統婚禮的影響 蔡南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台灣原住民,究竟何時、 ... 兩大類,一為「生蕃」(又稱高山蕃、蕃人、兇蕃、蕃、蕃民、野蕃、界外蕃及蕃族等);另一為「熟蕃」(又稱平地蕃、土蕃、歸化生蕃、良蕃、社蕃、歸化蕃、流蕃、平蕃。
Posted by Chopathar W Mache at 2011年11月08日 09:57
※このブログではブログの持ち主が承認した後、コメントが反映される設定で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