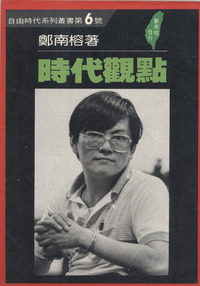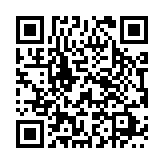2010年06月05日
歷史的餘震:嘉絨 2008年& 1775年

May 20th, 2010
TREMORS OF HISTORY: GYALRONG 2008 & 1775
歷史的餘震:嘉絨 2008年& 1775年
文/嘉央諾布
你或許以為在報導自然災難的時候,第一個原則是正確報導發生的地點,特別是在地震發生的時候,因為地震不像四處流動的洪水,或者行踪不定的颶風,是有一個可明白辨識的震央的。
剛開始的時候,紐約時報,BBC,CNN報導結古多的地震,提到它發生的地點,在「‧‧‧中國西部一個偏僻地區。」只有到後來,特別是當圖伯特僧侶穿著他們顯眼的絳紅色袍子,成百上千地大批參與救援工作,受災城鎮的圖伯特名字與該地區具有鮮明的圖伯特特色的事實,才為媒體所批露。世界對圖伯特大部份事務所罹患的廣泛失憶症,當然,是中國多年以來刻意更改圖伯特村子、城鎮、聚落、地方或者地標的名字、或以漢語拼音重新拼寫的結果,有時候甚至把這些地方整個搬遷,或是在行政上改易,或者乾脆地圖上重畫,最終的目的是希望消滅圖伯特所有地區的歷史與文化身份,好讓它們看起來一直就是中國的一部份--不然,就是想讓這些地區看起來像是沒有人居的荒郊野地,而中國現在正在想辦法開發發展。
2008年令人難過的地震,也得到這種充滿失憶症的對待,世界的媒體幾乎提起來時,總是說它是四川大地震,甚至一些圖伯特人也這麼說。(1) 四川省的漢地城市都江堰,理所當然地得到中國國內與西方媒體的最多的關注,因為它人命的損失是最嚴重的。然而這裏也應該提起,就是因為建築物的品質太過低劣(特別是學校),才造成人命損失這麼慘重,不光只是地震本身的威力,因為其震波的強度在其西邊的圖伯特地區更為劇烈。
事實上,地震的震央,是在圖伯特地區,也就是阿壩藏族自治州的Lungu(漢語拼音:Wenchuan ,汶川)。許多博巴也在附近的圖伯特地區裏遇難,包括甘孜州的Rongtrak (或稱Tenpa, 漢語拼音:Danba,丹巴),以及甘肅省的 Kanlho(漢語拼音:Gannan,甘南)州的Drugchu (漢語拼音:Zhouqu,舟曲)。當然,還有阿壩州的臥龍,也就是中國設立起他們的貓熊保護區的地方,也受到地震嚴重的影響。我向我的小孩解釋,臥龍的居民是圖伯特人,而那就是為什麼,這種行動笨拙、生育緩慢,以及根本上毫無防衛能力的貓熊能夠存活到現在的原因,相比之下,中國本土的所有野生動物(不管多敏捷、多詭密、多狡滑、多兇猛),早就都消失在廣州或其他地方,成為中國特色的肉品市場的俎上肉了。(見Colin Thubron, Behind the Wall, 頁 182-186, 190-192。)
阿壩自治州與其南部的區域,也就是現在隸屬甘孜自治州的地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分而治之、不公不正的行政區劃之前,乃是圖伯特的嘉絨,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偉大的學者卡爾梅‧桑丹提到,這個地區在博伊(藏文)的拼法是寫成 rGyal rong,是由全名 rGyal mo tsha ba rong(嘉莫察窪絨)所簡寫的。它與 rGyalmo dngul chu (嘉莫歐曲,意為女王的銀色溪澗,中文稱大渡河)是相關的。雖然現在被劃入了四川省,這整個地區實際在地理上與四川盆地並不相屬,以崇山峻嶺為兩地的分水嶺。桑丹拉告訴我們,「在圖伯特地理的詞彚上,這個地區被描寫為 rong,也就是『峽谷』之意。它是圖伯特的四大峽谷之一 ( rong chen bzhi)。這四大峽谷分別是:Kongpo-rong(公窩絨), Atag-rong(阿倒絨), Tsawa-rong(察窪絨) 和 Gyalmo-rong(嘉莫絨)。」(2) 桑丹拉也提到了有一個爭議是嘉絨究竟屬於康還是安多的問題。
在地震後,我坐下來想為嘉絨地方的人們寫一篇致敬的文章,然而三月大起義與後續發生的諸事,如中國的鎮壓,北京奧運等等,讓我分了心。又加上我對於該圖伯特地區不是特別了解,也使文章沒有進展。然而前一兩個星期,我不小心翻出1998年我曾經寫過,卻早被我忘記的,一篇有關於嘉絨的文章 (3)。我在這裏再把它重新貼出來,並加上一些新的資料。這一篇文章對於嘉絨的文化、人民、甚至歷史並沒有作太多的闡述,只針對那個地區所發生的一場戰爭作一個相當扼要的敘述。然而那是一場如何令人驚嘆的戰爭!我們也許可以稱它為圖伯特的溫泉關之役(Thermophylae),特別是考慮到此役中,斯巴達面對波斯大軍入侵時,希臘的其餘地方皆袖手旁觀緣故。然而如果我們思慮及當時特殊的政教因素,以及堅固的石頭碉堡與高明的工程技巧對於抵禦外敵者的重要性,那麼嘉絨此役說不定更應該與1565年聖約翰騎士團(Knights of St. John)奮勇作戰,擊退排山倒海的奧圖曼帝國大軍,那一段可歌可泣、保衛家園的史實相提並論。
十八世紀,滿洲的勢力在亞洲崛起之際,清朝的皇軍在圖伯特東部的嘉絨地區打了兩場曠日耗時的戰爭,此二役使得乾隆的其他戰役皆顯得小巫見大巫。雖然此二役是對兩個不怎麼龐大的圖伯特王國,促浸(Rabden)與儹拉(Tsanlha),所展開的攻擊,然而光光在費用上就耗費中國國庫六千一百萬兩(4),遠遠超過一七六零年代晚期遠征緬甸(九百萬兩),以及1788年與1792年針對廓爾喀的兩次戰役(軍費超過三百五十萬兩,而其間大部份的戰鬥皆由圖伯特兵勇負責)。而清朝征服伊犂與準噶爾之役,歷時五年(1755-1760年),所涉及的領土比嘉絨大上十倍,也只花費了二千三百萬兩,大約是兩次嘉絨之役的三分之一而已。(5) 除了嘉絨博巴的不屈不撓、高明的戰鬥技巧、奮勇禦敵的氣魄之外,此地之所以久攻不下,得以有效防守,巍峨屹立、凜然難犯的石塔與堡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譯注:中文史書裏稱「高碉」、「戰碉」,乾隆有詩曰:「堅碉林立」。)
即使只端詳這些壯觀石塔遺跡的照片,任何人都不免強烈地感覺到嘉絨哇(嘉絨人)在他們長期對抗中國帝國主義奮鬥中,挾著龐大的力量、高明的技術與科學工藝,給中國軍隊造成的壓力。這些高碉的形狀各有不同:方形、八角形、六角形、甚至是五角星形。我在某處讀到,這些獨特的形狀強化了這些建築物的結構,甚至可以承受得住地震的搖動。我們一定要銘記在心的是,這些建築都未使用水泥,或任何形式的砂漿(mortar),只有乾壁(dry wall)的技術,然而屬於一種非常成熟的工藝技巧。看到這些高碉的遺跡,對於曩昔圖伯特人所擁有的建築與工程技巧,不可能不感到驚奇讚歎、肅然起敬,當然,我們還有其他偉大的建築物,如布達拉宮、江孜袞本(譯:指江孜白居寺)、還有唐東傑布的鐵吊橋。
認為圖伯特文化除了佛教以外,即沒有其他什麼珍貴之處的喇嘛與修行之士,實在應該找一天,實地搬動石頭來修築這些碉堡,如同馬爾巴懲罰密勒日巴為邪惡的行徑贖罪一樣。
根據學者如榮振華(J. Dehergne)、羅書復(Luo Shufu, 音譯)、恆慕義(A. W. Hummel)等人的研究,「(嘉絨)這些石堡,假如不是清朝將領阿桂利用傅作霖指導建造的西洋火炮的話,可能是根本攻不下來的。」傅作霖(Felix da Rocha,1713-1781,1774年由欽天監副監正升監正),是一位葡萄牙的耶穌會士,為滿洲朝廷所終身僱用。「他不僅只負責這些特殊火炮的監造,(嘉央啦:也許還為了崎嶇地勢上的運輸目的而作特別的設計),而且他還負責『調查研究』,當這些火炮實際派上用場,將對大金川作出主要的攻擊時,他也在1774年年底親臨前線。」(大金川,是中國對Rabden的稱謂。)(6)
在拉薩的甘丹頗章政府,完全不把滿清的攻擊當成對於圖伯特友邦的侵略,反而認為這是大好機會,可以藉此擊敗宗教的夙敵--因為嘉絨是本教的最後據點。乾隆皇帝的佛教上師,格魯巴喇嘛,章嘉呼圖克圖若必多吉(Changkya Hutoktu Rolpae Dorjee, 1717-86),甚至為了嘉絨本波(本教徒)之戰敗與毀滅舉行了一個特別的法事,祈求「文殊菩薩轉世」,乾隆皇帝之勝利大捷。1775年,促浸國的最後一座偉大戰碉,在耶穌會士的西洋火炮攻擊之下,或可能在格魯巴的法力保祐之下,終於陷落。同一年,清朝的皇軍摧毀了促浸王室輝煌的本教寺院,雍仲拉頂寺(Yundrung Lhateng),並在原址上重建新的格魯巴寺院。
這兩次對嘉絨的軍事攻擊,使清朝的財庫元氣大傷,再加上接下來五十年裏,中國全國的經費進一步遭到耗竭,清朝自此一蹶不振,江河日下,再也無法重登昔時帝國權力之巔峰。
(註:有人告訴我嘉絨在1956年揭竿而起,反抗中共的佔領軍。假如有更進一步的相關資訊,敬請惠賜,不勝感激。)
References:
1.Tsewang Namyal “Jyekundo Earthquake - Next Steps and Lessons” Phayul, April 22
2. Samten G. Karmay, Feast of the Morning Ligh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od-engravings of Shenrab’s Life-stories and the Bon Canon from Gyalrong, 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 57,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Osaka 2005.
3. Jamyang Norbu, “Missionary Cannons Defeat the Tibetans of Gyalrong”, Lungta, Tibet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MI, Dharamshala, Vol II Winter 1998.
4.Tael (兩; pinyin: liǎng) was a measure of silver about 40gms. Modern studies suggest that, on purchasing power party basis, one tael of silver was worth about 4130 modern Chinese yuan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660.8 in the mid Ming dynasty.
5.Dan Martin, “Bonpo Canons and Jesuit Cannons”, The Tibet Journal Vol.XV No.2 Summer 1990, Dharamshala.
6. Roger Greatrex,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Jinchuan War 1747-1749)”,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I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Oslo, 1994
譯按:文中所提到的溫泉關之役,就是2007年好萊塢電影:《300壯士:斯巴達的逆襲》所根據的古代歷史戰役。

TREMORS OF HISTORY: GYALRONG 2008 & 1775
歷史的餘震:嘉絨 2008年& 1775年
文/嘉央諾布
你或許以為在報導自然災難的時候,第一個原則是正確報導發生的地點,特別是在地震發生的時候,因為地震不像四處流動的洪水,或者行踪不定的颶風,是有一個可明白辨識的震央的。
剛開始的時候,紐約時報,BBC,CNN報導結古多的地震,提到它發生的地點,在「‧‧‧中國西部一個偏僻地區。」只有到後來,特別是當圖伯特僧侶穿著他們顯眼的絳紅色袍子,成百上千地大批參與救援工作,受災城鎮的圖伯特名字與該地區具有鮮明的圖伯特特色的事實,才為媒體所批露。世界對圖伯特大部份事務所罹患的廣泛失憶症,當然,是中國多年以來刻意更改圖伯特村子、城鎮、聚落、地方或者地標的名字、或以漢語拼音重新拼寫的結果,有時候甚至把這些地方整個搬遷,或是在行政上改易,或者乾脆地圖上重畫,最終的目的是希望消滅圖伯特所有地區的歷史與文化身份,好讓它們看起來一直就是中國的一部份--不然,就是想讓這些地區看起來像是沒有人居的荒郊野地,而中國現在正在想辦法開發發展。
2008年令人難過的地震,也得到這種充滿失憶症的對待,世界的媒體幾乎提起來時,總是說它是四川大地震,甚至一些圖伯特人也這麼說。(1) 四川省的漢地城市都江堰,理所當然地得到中國國內與西方媒體的最多的關注,因為它人命的損失是最嚴重的。然而這裏也應該提起,就是因為建築物的品質太過低劣(特別是學校),才造成人命損失這麼慘重,不光只是地震本身的威力,因為其震波的強度在其西邊的圖伯特地區更為劇烈。
事實上,地震的震央,是在圖伯特地區,也就是阿壩藏族自治州的Lungu(漢語拼音:Wenchuan ,汶川)。許多博巴也在附近的圖伯特地區裏遇難,包括甘孜州的Rongtrak (或稱Tenpa, 漢語拼音:Danba,丹巴),以及甘肅省的 Kanlho(漢語拼音:Gannan,甘南)州的Drugchu (漢語拼音:Zhouqu,舟曲)。當然,還有阿壩州的臥龍,也就是中國設立起他們的貓熊保護區的地方,也受到地震嚴重的影響。我向我的小孩解釋,臥龍的居民是圖伯特人,而那就是為什麼,這種行動笨拙、生育緩慢,以及根本上毫無防衛能力的貓熊能夠存活到現在的原因,相比之下,中國本土的所有野生動物(不管多敏捷、多詭密、多狡滑、多兇猛),早就都消失在廣州或其他地方,成為中國特色的肉品市場的俎上肉了。(見Colin Thubron, Behind the Wall, 頁 182-186, 190-192。)
阿壩自治州與其南部的區域,也就是現在隸屬甘孜自治州的地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分而治之、不公不正的行政區劃之前,乃是圖伯特的嘉絨,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偉大的學者卡爾梅‧桑丹提到,這個地區在博伊(藏文)的拼法是寫成 rGyal rong,是由全名 rGyal mo tsha ba rong(嘉莫察窪絨)所簡寫的。它與 rGyalmo dngul chu (嘉莫歐曲,意為女王的銀色溪澗,中文稱大渡河)是相關的。雖然現在被劃入了四川省,這整個地區實際在地理上與四川盆地並不相屬,以崇山峻嶺為兩地的分水嶺。桑丹拉告訴我們,「在圖伯特地理的詞彚上,這個地區被描寫為 rong,也就是『峽谷』之意。它是圖伯特的四大峽谷之一 ( rong chen bzhi)。這四大峽谷分別是:Kongpo-rong(公窩絨), Atag-rong(阿倒絨), Tsawa-rong(察窪絨) 和 Gyalmo-rong(嘉莫絨)。」(2) 桑丹拉也提到了有一個爭議是嘉絨究竟屬於康還是安多的問題。
在地震後,我坐下來想為嘉絨地方的人們寫一篇致敬的文章,然而三月大起義與後續發生的諸事,如中國的鎮壓,北京奧運等等,讓我分了心。又加上我對於該圖伯特地區不是特別了解,也使文章沒有進展。然而前一兩個星期,我不小心翻出1998年我曾經寫過,卻早被我忘記的,一篇有關於嘉絨的文章 (3)。我在這裏再把它重新貼出來,並加上一些新的資料。這一篇文章對於嘉絨的文化、人民、甚至歷史並沒有作太多的闡述,只針對那個地區所發生的一場戰爭作一個相當扼要的敘述。然而那是一場如何令人驚嘆的戰爭!我們也許可以稱它為圖伯特的溫泉關之役(Thermophylae),特別是考慮到此役中,斯巴達面對波斯大軍入侵時,希臘的其餘地方皆袖手旁觀緣故。然而如果我們思慮及當時特殊的政教因素,以及堅固的石頭碉堡與高明的工程技巧對於抵禦外敵者的重要性,那麼嘉絨此役說不定更應該與1565年聖約翰騎士團(Knights of St. John)奮勇作戰,擊退排山倒海的奧圖曼帝國大軍,那一段可歌可泣、保衛家園的史實相提並論。
十八世紀,滿洲的勢力在亞洲崛起之際,清朝的皇軍在圖伯特東部的嘉絨地區打了兩場曠日耗時的戰爭,此二役使得乾隆的其他戰役皆顯得小巫見大巫。雖然此二役是對兩個不怎麼龐大的圖伯特王國,促浸(Rabden)與儹拉(Tsanlha),所展開的攻擊,然而光光在費用上就耗費中國國庫六千一百萬兩(4),遠遠超過一七六零年代晚期遠征緬甸(九百萬兩),以及1788年與1792年針對廓爾喀的兩次戰役(軍費超過三百五十萬兩,而其間大部份的戰鬥皆由圖伯特兵勇負責)。而清朝征服伊犂與準噶爾之役,歷時五年(1755-1760年),所涉及的領土比嘉絨大上十倍,也只花費了二千三百萬兩,大約是兩次嘉絨之役的三分之一而已。(5) 除了嘉絨博巴的不屈不撓、高明的戰鬥技巧、奮勇禦敵的氣魄之外,此地之所以久攻不下,得以有效防守,巍峨屹立、凜然難犯的石塔與堡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譯注:中文史書裏稱「高碉」、「戰碉」,乾隆有詩曰:「堅碉林立」。)
即使只端詳這些壯觀石塔遺跡的照片,任何人都不免強烈地感覺到嘉絨哇(嘉絨人)在他們長期對抗中國帝國主義奮鬥中,挾著龐大的力量、高明的技術與科學工藝,給中國軍隊造成的壓力。這些高碉的形狀各有不同:方形、八角形、六角形、甚至是五角星形。我在某處讀到,這些獨特的形狀強化了這些建築物的結構,甚至可以承受得住地震的搖動。我們一定要銘記在心的是,這些建築都未使用水泥,或任何形式的砂漿(mortar),只有乾壁(dry wall)的技術,然而屬於一種非常成熟的工藝技巧。看到這些高碉的遺跡,對於曩昔圖伯特人所擁有的建築與工程技巧,不可能不感到驚奇讚歎、肅然起敬,當然,我們還有其他偉大的建築物,如布達拉宮、江孜袞本(譯:指江孜白居寺)、還有唐東傑布的鐵吊橋。
認為圖伯特文化除了佛教以外,即沒有其他什麼珍貴之處的喇嘛與修行之士,實在應該找一天,實地搬動石頭來修築這些碉堡,如同馬爾巴懲罰密勒日巴為邪惡的行徑贖罪一樣。
根據學者如榮振華(J. Dehergne)、羅書復(Luo Shufu, 音譯)、恆慕義(A. W. Hummel)等人的研究,「(嘉絨)這些石堡,假如不是清朝將領阿桂利用傅作霖指導建造的西洋火炮的話,可能是根本攻不下來的。」傅作霖(Felix da Rocha,1713-1781,1774年由欽天監副監正升監正),是一位葡萄牙的耶穌會士,為滿洲朝廷所終身僱用。「他不僅只負責這些特殊火炮的監造,(嘉央啦:也許還為了崎嶇地勢上的運輸目的而作特別的設計),而且他還負責『調查研究』,當這些火炮實際派上用場,將對大金川作出主要的攻擊時,他也在1774年年底親臨前線。」(大金川,是中國對Rabden的稱謂。)(6)
在拉薩的甘丹頗章政府,完全不把滿清的攻擊當成對於圖伯特友邦的侵略,反而認為這是大好機會,可以藉此擊敗宗教的夙敵--因為嘉絨是本教的最後據點。乾隆皇帝的佛教上師,格魯巴喇嘛,章嘉呼圖克圖若必多吉(Changkya Hutoktu Rolpae Dorjee, 1717-86),甚至為了嘉絨本波(本教徒)之戰敗與毀滅舉行了一個特別的法事,祈求「文殊菩薩轉世」,乾隆皇帝之勝利大捷。1775年,促浸國的最後一座偉大戰碉,在耶穌會士的西洋火炮攻擊之下,或可能在格魯巴的法力保祐之下,終於陷落。同一年,清朝的皇軍摧毀了促浸王室輝煌的本教寺院,雍仲拉頂寺(Yundrung Lhateng),並在原址上重建新的格魯巴寺院。
這兩次對嘉絨的軍事攻擊,使清朝的財庫元氣大傷,再加上接下來五十年裏,中國全國的經費進一步遭到耗竭,清朝自此一蹶不振,江河日下,再也無法重登昔時帝國權力之巔峰。
(註:有人告訴我嘉絨在1956年揭竿而起,反抗中共的佔領軍。假如有更進一步的相關資訊,敬請惠賜,不勝感激。)
References:
1.Tsewang Namyal “Jyekundo Earthquake - Next Steps and Lessons” Phayul, April 22
2. Samten G. Karmay, Feast of the Morning Ligh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od-engravings of Shenrab’s Life-stories and the Bon Canon from Gyalrong, 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 57,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Osaka 2005.
3. Jamyang Norbu, “Missionary Cannons Defeat the Tibetans of Gyalrong”, Lungta, Tibet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MI, Dharamshala, Vol II Winter 1998.
4.Tael (兩; pinyin: liǎng) was a measure of silver about 40gms. Modern studies suggest that, on purchasing power party basis, one tael of silver was worth about 4130 modern Chinese yuan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660.8 in the mid Ming dynasty.
5.Dan Martin, “Bonpo Canons and Jesuit Cannons”, The Tibet Journal Vol.XV No.2 Summer 1990, Dharamshala.
6. Roger Greatrex,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Jinchuan War 1747-1749)”,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I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Oslo, 1994
譯按:文中所提到的溫泉關之役,就是2007年好萊塢電影:《300壯士:斯巴達的逆襲》所根據的古代歷史戰役。

Posted by rosaceae at 01:50
│嘉央諾布啦
留言
悬钩子一如既往的美妙翻译!
感恩~请继续~加素切~
——一位境内博弥
感恩~请继续~加素切~
——一位境内博弥
Posted by Apollocean at 2010年06月05日 22:57
嘉绒确实在1956年揭竿而起。由于缺乏资料,无法了解真实的死亡人数。但从中共资料记载的部分战斗中,战争的激烈情形可见一斑:
1956年3月13日,解放军一部在阿坝州的直威寨遭到苍旺洛部伏击,九人被打死。
1956年3月13日,一支中共工作队在赴绰斯甲上寨区(今阿坝州壤塘县上寨区)途中遭到苍旺洛部伏击,工作队的33名中共干部中只有1人逃掉(被击伤),其余32人中死亡30人、被俘1人、叛变1人。
1956年阿坝州南坪县(今九寨沟县)东北部落的十余名战士伏击了中共土改工作组,打死民警队队长和一名干部。
1956年5月3日,解放军一个排在阿坝州的毛儿盖被“叛匪”围攻,解放军在突围时阵亡12人、伤7人。
1956年5月8日,阿坝州马尔康县达维乡(现康山乡)民主改革工作队被“叛匪”围攻,在战斗中一名中共民兵叛变,其余八名工作队员全部被歼灭,无一人生还。
1956年5月26日,阿坝州黑水县石碉楼乡格衣村的工作组在突围时全部阵亡。
1956年5月末,解放军两个营进抵阿坝州黑水县的芦花,企图剿灭麻窝的“叛匪”,但作战不利,被迫撤退,在撤退时负责掩护的一个班全部阵亡。解放军在这次战斗中共阵亡11人、伤15人。
1957年3月23日,驻阿坝州阿坝县查理寺的解放军某部遭到伏击,死亡4人、伤1人。
1958年10月10日,解放军骑兵1团一部在阿坝州的若柯盯上了一支三十余人的“叛匪”,企图在拂晓时对其营地发动偷袭,因被对方发现,解放军反而遭到包围。11日解放军派出一个加强连增援,因畏敌而撤回,使解围落空,导致解放军阵亡17人。
1958年10月25日拂晓,解放军进至阿坝州活尔龙果东北森林附近,开始围剿隐匿在森林内的8名“叛匪”,但遭到顽强抵抗,26日20时才结束战斗。以文甲为首的8名“叛匪”全部战死,但解放军也付出了伤亡19人的惨重代价,并消耗各种子弹5092发。
1959年4月3日,阿坝州阿坝县武装民警队一部33人被“土匪”袭击,死亡7人、伤2人。
……
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出了名的左棍,曾因拒绝出面接待达赖喇嘛引起周恩来不快,他在主政四川期间导致几百万人饿死,就是这样的人却受到毛泽东重用。藏人受到的压迫可想而知,不反抗才怪。所谓的“民主改革”,说的好听,纯粹是骗鬼的。
1956年3月13日,解放军一部在阿坝州的直威寨遭到苍旺洛部伏击,九人被打死。
1956年3月13日,一支中共工作队在赴绰斯甲上寨区(今阿坝州壤塘县上寨区)途中遭到苍旺洛部伏击,工作队的33名中共干部中只有1人逃掉(被击伤),其余32人中死亡30人、被俘1人、叛变1人。
1956年阿坝州南坪县(今九寨沟县)东北部落的十余名战士伏击了中共土改工作组,打死民警队队长和一名干部。
1956年5月3日,解放军一个排在阿坝州的毛儿盖被“叛匪”围攻,解放军在突围时阵亡12人、伤7人。
1956年5月8日,阿坝州马尔康县达维乡(现康山乡)民主改革工作队被“叛匪”围攻,在战斗中一名中共民兵叛变,其余八名工作队员全部被歼灭,无一人生还。
1956年5月26日,阿坝州黑水县石碉楼乡格衣村的工作组在突围时全部阵亡。
1956年5月末,解放军两个营进抵阿坝州黑水县的芦花,企图剿灭麻窝的“叛匪”,但作战不利,被迫撤退,在撤退时负责掩护的一个班全部阵亡。解放军在这次战斗中共阵亡11人、伤15人。
1957年3月23日,驻阿坝州阿坝县查理寺的解放军某部遭到伏击,死亡4人、伤1人。
1958年10月10日,解放军骑兵1团一部在阿坝州的若柯盯上了一支三十余人的“叛匪”,企图在拂晓时对其营地发动偷袭,因被对方发现,解放军反而遭到包围。11日解放军派出一个加强连增援,因畏敌而撤回,使解围落空,导致解放军阵亡17人。
1958年10月25日拂晓,解放军进至阿坝州活尔龙果东北森林附近,开始围剿隐匿在森林内的8名“叛匪”,但遭到顽强抵抗,26日20时才结束战斗。以文甲为首的8名“叛匪”全部战死,但解放军也付出了伤亡19人的惨重代价,并消耗各种子弹5092发。
1959年4月3日,阿坝州阿坝县武装民警队一部33人被“土匪”袭击,死亡7人、伤2人。
……
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出了名的左棍,曾因拒绝出面接待达赖喇嘛引起周恩来不快,他在主政四川期间导致几百万人饿死,就是这样的人却受到毛泽东重用。藏人受到的压迫可想而知,不反抗才怪。所谓的“民主改革”,说的好听,纯粹是骗鬼的。
Posted by 半夜鸡不叫 at 2010年06月07日 12:24
以前在中国军事网络上差的到,从汶川到黑水剿匪五万六千余人。那些都是嘉荣人吧
Posted by 大家诶 at 2010年10月10日 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