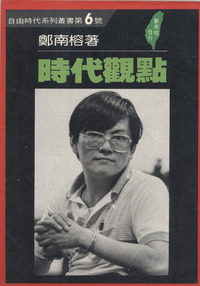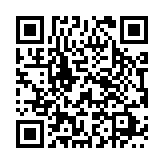2011年05月22日
達瓦才仁:回覆台灣懸鉤子的公開信
台灣懸鉤子:達瓦才仁董事長的公開信寄給我時,我人在北京,沒有辦法翻牆,所以只能擱著。現在我已經回到台灣自由世界,當然應該把學問淵博、自成一家之言的達瓦才仁董事長公開信另成一篇。領教了~
回覆台灣懸鉤子的公開信
by 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
一、背景說明
日前很榮幸地參加懸鉤子《龍在西藏》(懸鉤子:是《龍在雪域》)在台灣的新書發表會,因為該書和她的另一個佳作《被遮蔽的圖伯特》(懸鉤子:是《遮蔽的圖伯特》)一直都是我想要先讀為快的兩本書。
發表會上不少人對於西藏民眾選擇「中間道路」提出了一些看法,認為那並非真正代表西藏民眾的選擇等等。這種說法並不新鮮,其言外之意是達賴喇嘛並不是真正代表西藏民眾的意志,甚至隱含著西藏民眾除了唯命是從外不懂得自己抉擇。因此,我感到有責任需要做出說明──「中間道路」是西藏民眾透過民主程序做出的決定,而且,西藏民族並不是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蒙昧。正如顙東仁波切曾指出︰「有很多人攻擊接受達賴喇嘛理念的民眾是『迷信』、『不會獨立思考』、『不負責任』,那是對西藏民眾不敬的言論。」
達賴喇嘛於今年3月19日在達蘭薩拉的講話中也非常清楚地指出西藏人所以選擇「中間道路」是因為:「這是我們對諸多元素通盤考量後慎重作出的決定。最主要的是,我見過許多西藏境內的知識份子和年輕人,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裡見過很多人,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指出︰中間道路符合實際,具有可操作性,並贏得眾多華人知識份子的支持,是確實可行的途徑。我們這邊有一些人,嘴上常掛著西藏境內民眾希望西藏獨立的言論。當然,如果不經過任何思考地回答你要獨立還是自治的問題,則肯定會選擇獨立。如果獨立可以在街道上隨意撿拾或取得,則當然沒有問題,可實際並不是這樣。因此,需要對諸多原素進行考量後做出決定。」
達賴喇嘛因此要求那些人︰「不要再不經思考地宣稱-境內的廣大西藏民眾要求獨立,是達賴喇嘛反對獨立等言論。」
懸鉤子的公開信中談到一些人對我的言論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是針對上述內容,則我仍會繼續堅持,因為對此作出說明是我的責任。但如果是針對我對「西藏」概念的說法,則可能有些誤會,當然主要的責任是我沒有解釋清楚,我就藉此機會簡略說明如下:
回覆台灣懸鉤子的公開信
by 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
一、背景說明
日前很榮幸地參加懸鉤子《龍在西藏》(懸鉤子:是《龍在雪域》)在台灣的新書發表會,因為該書和她的另一個佳作《被遮蔽的圖伯特》(懸鉤子:是《遮蔽的圖伯特》)一直都是我想要先讀為快的兩本書。
發表會上不少人對於西藏民眾選擇「中間道路」提出了一些看法,認為那並非真正代表西藏民眾的選擇等等。這種說法並不新鮮,其言外之意是達賴喇嘛並不是真正代表西藏民眾的意志,甚至隱含著西藏民眾除了唯命是從外不懂得自己抉擇。因此,我感到有責任需要做出說明──「中間道路」是西藏民眾透過民主程序做出的決定,而且,西藏民族並不是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蒙昧。正如顙東仁波切曾指出︰「有很多人攻擊接受達賴喇嘛理念的民眾是『迷信』、『不會獨立思考』、『不負責任』,那是對西藏民眾不敬的言論。」
達賴喇嘛於今年3月19日在達蘭薩拉的講話中也非常清楚地指出西藏人所以選擇「中間道路」是因為:「這是我們對諸多元素通盤考量後慎重作出的決定。最主要的是,我見過許多西藏境內的知識份子和年輕人,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裡見過很多人,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指出︰中間道路符合實際,具有可操作性,並贏得眾多華人知識份子的支持,是確實可行的途徑。我們這邊有一些人,嘴上常掛著西藏境內民眾希望西藏獨立的言論。當然,如果不經過任何思考地回答你要獨立還是自治的問題,則肯定會選擇獨立。如果獨立可以在街道上隨意撿拾或取得,則當然沒有問題,可實際並不是這樣。因此,需要對諸多原素進行考量後做出決定。」
達賴喇嘛因此要求那些人︰「不要再不經思考地宣稱-境內的廣大西藏民眾要求獨立,是達賴喇嘛反對獨立等言論。」
懸鉤子的公開信中談到一些人對我的言論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是針對上述內容,則我仍會繼續堅持,因為對此作出說明是我的責任。但如果是針對我對「西藏」概念的說法,則可能有些誤會,當然主要的責任是我沒有解釋清楚,我就藉此機會簡略說明如下:
二、「西藏」代表的是王朝
很多人一說到「西藏」,第一個想法就是從藏文「藏」(Gtsang)的意義解釋,這沒有錯。但大家都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中文「西藏」所指不論從內涵或外延,從來都不是藏文Gtsang的意思。
就現有資料而言,「西藏」第一次出現在中文裡,是西元1575年5月15日、明朝萬曆三年的史料中︰「蓋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見梁本、館本的《明實錄》卷三十七,頁2-3。)那時間正好跟西元1565年建立的西藏藏巴王朝是同一時期。藏巴王朝定都日喀則(藏地方的首府),藏人因此稱其為藏巴王朝,中文史料則普遍稱為藏巴汗。
因此,唯一的解釋是「西藏」是由當時的王朝名稱所衍生。再聯想到中文史料稱「大夏國」為「西夏」。將藏巴王朝視為朝代名稱並冠予方位,也就順理成章稱為「西藏」了。簡而言之,西藏的產生過程是︰地區名→朝代名→西藏,或者說︰藏→藏巴王朝→西藏。所以,「西藏」一詞直接對應的是「藏巴王朝」,而不是藏巴王朝的詞源「Gtsang」這個地區名稱。
中國藏學家陳慶英認為「西藏」一詞最早出現於清朝滿文奏章中,應該是滿文「西部藏」意思的漢譯。雖然如前所述,滿文檔案的「西藏」並非是第一次出現,但上述兩個來源相互並不矛盾,或者說具有互補性。因為滿清和西藏初次建立聯繫的時候,西藏還在藏巴王朝末期,達賴喇嘛的代表到盛京見滿清皇帝時,滿清皇帝的回禮中就有給藏巴汗的信件和禮物。這其實也反證了「西藏」是源於藏巴王朝的,因為除了藏巴王朝,實在找不到理由說明為何在明朝大臣或滿清皇帝的視野中竟然會出現「西藏」這個詞彙。正如漢族的稱呼源於漢朝,唐人的稱呼源於唐朝一樣,西藏這個稱呼也源於西藏歷史上的藏巴王朝。而達賴喇嘛領導的噶登頗章政權就是在推翻藏巴王朝後建立的。
另外,不論何時,「西藏」從來都沒有用來指稱「Gtsang」地方。同樣,不論何時,「西藏」一詞都能夠實現「民族和地域」的雙重指代功能︰西藏人=西藏民族,西藏語=西藏民族語言,西藏服裝=西藏民族服裝等等。此外,正如十七條協議的前言中多次出現「西藏民族」這個概念,表明共產黨也並不認為「西藏」只是一個地區的名稱。
如果說歷史上「西藏」的範圍曾有大有小,那只是根據藏民族建立的政權所控制地方之大小而隨之發生變動。
還有,西藏一詞並不是到國民黨時候才普遍使用,而是在滿清中後期就已經普遍使用。我記得乾隆皇帝立在拉薩的石碑中,就已經是「西藏」和「圖伯特」混用,而且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從那以後,滿清的資料中一般都以西藏稱呼之。在此之前,稱呼「西藏」的較少,但不是沒有,如西元1699年滿清將領岳升的奏章中就寫「臣查打箭爐各處地方,向系藏人霸佔。」等。而一直到七世達賴喇嘛為止,西藏政府的統治範圍是包括整個西藏三區的。
其他還可以舉出一些理由,但我覺得以上就足夠了。
三、我不反對使用「圖伯特」,但反對取代「西藏」。
我的一些朋友也不喜歡使用「西藏」這個概念,我都是建議他們使用圖伯特。因為這是從西元八世紀開始就有的稱呼,第一次是出現在西元八世紀回紇汗王(現維吾爾或廣義的突厥)的碑文,而且也與英文等直譯相配合。
但我反對一些人主張的用「圖伯特」取代「西藏」的觀點。這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是沒有意義。 因為,不論「圖伯特」或「西藏」,翻譯成藏文都是「bod」。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圖伯特」或「西藏」的內涵外延只能根據藏文「bod」來定義,這就足夠了。
而且,在中文史料中,「西藏」也使用了幾個世紀,難道在此期間中文史料中的「西藏」所指的竟然是只有幾十年歷史之共產黨的「西藏自治區」或是範圍更小的國民黨的「西藏地方」?抑或是藏文的Gtsang地方?近代而言,《十七條協議》有藏中兩種文本,「西藏」與對應的「bod」所指的難道是「西藏自治區」?或是國民黨的「西藏地方」?
再往後,聯合國曾透過有關西藏的決議,中文是聯合國的法定用語,決議中文版使用的是「西藏」這個詞彙。難道我們認為聯合國透過的有關西藏的決議所涵蓋的範圍只有「西藏自治區」或是「西藏地方」?而另一個問題是︰簽定十七條協議或聯合國透過決議時,「西藏自治區」還連個影子都沒有,而「西藏地方」不僅範圍比「西藏自治區」小將近一半,而且主張這個概念的國民黨已經被趕出了中國。
如上述,我並不反對使用「圖伯特」,正如滿清皇帝在拉薩的碑文中那樣,「圖伯特」和「西藏」可以並用,因為兩者都是外民族對「bod」的指稱,並不存在高低上下的涵義。也因此,我反對以「圖伯特」等來取代「西藏」或廢棄使用「西藏」。
另外,我反對西藏議會使用「圖博」的決議,認為「圖博」這個詞彙是一個沒有歷史根據或現實基礎的人造概念。中文史料上從未使用「圖博」這個詞彙,這是一個憑空人造,沒有人知道出處,也沒辦法望文生義,更沒有被任何辭典所收錄的新詞彙。
懸鉤子質問我:「我請您捫心自問,西藏一詞是為了博巴長遠的利益著想嗎?您一個人武斷地自認可以代表所有博巴,專斷地決定了所有博巴的國名,您如此作法,究竟獲得了誰的授權(mandate)?其民意基礎又何在?您對得起先人正名的努力與苦心嗎?未來的子子孫孫就該這樣永遠屈從,以中國人的意旨為意旨?」
對懸鉤子的質問和公開信,我發自內心地充滿感激,因為其中表現的是對西藏一片真情摯意的關懷。同樣,我是一個西藏人,我對自己的立場有明確的認知,這不會受在中國或在台灣或美國受教育所影響,我們的任何選擇都要考量歷史、現實以及西藏民族的長遠利益等不同層面。也因此,我才會強烈反對西藏議會有關使用「圖博」(注意,不是「圖伯特」),停止使用「西藏」的決議。當然,我提出反對意見不需要誰授權,因為這是我在行使言論自由。自然也談不上武斷,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權力和資格。正如我前面指出的那樣,流亡西藏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反對意見和理由。當時,支持和反對雙方之間進行過辯論,開過研討會,也曾分別寫辯駁文章等,這一切以後,西藏流亡政府和議會接受了我的意見,繼續使用「西藏」一詞,僅此而已。
台灣由於西藏流亡議會曾通過的決議而陰差陽錯地普遍使用「圖博」,這是一個錯誤造成的誤解。當然,現下有不少人將其視為台灣抵制中國本位主義的符號,如此則又另當別論了。
四、有關正名
懸鉤子的信中談到了正名問題,而且非常正確地指出︰「就如同目前圖伯特境內所出現的康定、久治、西寧這些地名所暗示的,外來統治者正忙著切斷被統治者的文化根源,其心昭昭。」
清人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中說︰「滅人之國,必先滅人之史,史亡則國亡。」 懸勾子上述切斷文化根源等,其實就是「滅史」的表現之一。
大部分被統治、被殖民的民族都只能面對這一切,就像台灣原住民在日據時代改日本姓名說日語,國民黨蔣家時代改漢姓說漢語一樣,很多被滿清國民共黨統治地區的藏人也被迫起漢姓漢名;不論滿清國民或共產,他們在佔領西藏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設立官府和建立學校,官府代表征服,學校則成為消滅自己的民族史、灌輸統治民族歷史和價值觀的同化(滅史後的結果)工具。其最終目的都是要消滅西藏民族。
「滅史」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讓其完全消失;另一種是改頭換面,留其殼,改變其內涵外延。而中共對「西藏」採取的恰恰是後者。如前所述,「西藏」得名於藏巴王朝,是一個西藏的朝代所衍生出來的概念,但中共卻極力避免提及或掩蓋這個事實和過程,而是取其與藏文「Gtsang」的聯繫,並且強化之、等同之,給人一種西藏的範圍僅限於「Gtsang」或所謂「前後藏」地區,以及史料中西藏的活動範圍僅限於「Gtsang」地方的印象,從而使其「分而治之」西藏的政策合理化等。
簡單地說,如果西藏人贊成棄用「西藏」,就等於承認中共對「西藏」的解釋;就等於承認中文史料中記載的「西藏」,以及十七條協議或聯合國決議等所有出現中文「西藏」詞彙者,其所指範圍僅限於西藏自治區或「Gtsang」地方。那怕僅僅是從功利的角度而言,這樣對西藏又有什麼好處?
綜上說述,「西藏」這個詞彙本身,並不是「兼具有占地野心與帝國主義的」的辭彙,也不是「帝國主義的中國所使用、縮限(說直接一點,就是矮化)的名詞」,相反,它實際上表現的是西藏歷史上的一個朝代,一個國家,一個獨立的政權。也因此,不使用它,承認中共對此的定義,漠視或放棄它原來所具有的歷史涵義等,那才是真正的「以中國人的意旨為意旨」。
五、其他的一些問題
信中談到「這樣的說法不正是您說的『博巴不追求基本人權,只要生存』的論調?」
我不知道我的原話是否表達清楚。我平常所說的是「西藏人追求的還不是人權,人權對西藏人而言是奢侈品;西藏人尋求的是民族的生存。」我還會強調︰「人權是活的好不好的問題,而對我們西藏民族而言,面臨的問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如果這個論調有什麼問題,那是我的責任。
公開信中還談到:「當時的格桑澤仁大概不會想到時隔不及百年,博巴後人就已經決定自廢武功,為了遷就中國,連族名都可以不必堅持了」。
這個世界的絕大部分民族都有自稱和他稱,這兩者並不一定是一致的。如中文的「土族」,藏語稱為「霍爾」,蒙古人稱其為「白韃靼」,他們自稱則是「蒙古爾」。我想,不會有人要求中國人、西藏人或蒙古人放棄原有的他稱,改而統稱「蒙古爾」吧!堅持族名指的是自稱的堅持。至於他稱,除非有侮蔑、歧視或貶損之涵義存在,否則,看不出有提出改變的必要。正如我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西藏」並不具有歧視或貶損的意思,和圖伯特、唐古特、菩提亞等一樣,都是外人對自稱「bod」之民族的他稱。
至於格桑澤仁等人,他們對西藏人而言,就像中國的汪精衛,肯定不配稱為我們的前人。他們都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分,承認國民黨對「西藏地方」的定義,因此,即使如願改名,「西藏地方」的實質不會有任何改變。我按公開信的網址看了該文,當時的西藏獨立地位可謂是舉世公認,但這些活寶卻在中國議會提出在西藏修建鐵路的議案,格桑澤仁就詢問「康青、青藏兩公路之保養及利用」的問題。就像改族名一樣,他們不過是在根本不是問題的地方找問題,卻迴避或不敢正視真正的問題──西藏民族世居之地就叫「西藏」。
如此等等,我就不一一解釋了。最後,不論我們的立場或觀點是否相同,我發自內心地充滿感激,因為懸鉤子的公開信中表現的是對西藏一片真情摯意的關懷。感恩關心西藏的諸位朋友。謝謝。
達瓦敬俱2011/05/12
附錄:
《明實錄》
萬曆三年四月甲戍(1575年5月15日)
俺答子賓兔,役屬作兒革、白利等諸番。隨令寄信松潘番、漢,以迎佛蓋寺為名,屢傳衅息。四川撫臣曾省吾、按臣郭莊以聞。謂:「宜速行陝西總督諭令順義王俺答,嚴戢賓兔,無得垂涎邊境,自敗盟好。」於是,兵科給書中蔡汝賢奏言:「賓兔蠶食諸番,撤我藩籬,逆志固已萌矣。議者不察,猶欲傳諭俺答,鈐制賓兔。夫奄奄病酋,墓木已拱,安能繫諸酋之手足耶?且賓兔前搶西寧,已行戒諭,曾莫之忌,可見於前事矣。乞敕該部亟咨該鎮,勘破虜情,整搠邊備,或先事以伐其謀,或遣諜以携其黨,或增兵以扼其隘,或相機以挫其鋒,令犯順者創,脅從者解,狂虜聞之,少知斂戢爾。且虜自稱貢以來,所要我者屢變,索鍋而與之鍋,求市而與之市,增馬而與之增,將來邊計安知底止!乃若巴蜀之衅,又自焚修之說啟也。蓋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彼黠虜豈真有從善之念哉!其挾詐用術,遠交近攻,不獨賓兔為然明矣。惟天語叮嚀當事諸臣毋蹈往轍,克勵新圖,無苟取一時之安,重貽他日之悔。」章下兵部。
梁本卷三七‧頁二下-三下 館本卷三七‧頁二下-三上
很多人一說到「西藏」,第一個想法就是從藏文「藏」(Gtsang)的意義解釋,這沒有錯。但大家都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中文「西藏」所指不論從內涵或外延,從來都不是藏文Gtsang的意思。
就現有資料而言,「西藏」第一次出現在中文裡,是西元1575年5月15日、明朝萬曆三年的史料中︰「蓋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見梁本、館本的《明實錄》卷三十七,頁2-3。)那時間正好跟西元1565年建立的西藏藏巴王朝是同一時期。藏巴王朝定都日喀則(藏地方的首府),藏人因此稱其為藏巴王朝,中文史料則普遍稱為藏巴汗。
因此,唯一的解釋是「西藏」是由當時的王朝名稱所衍生。再聯想到中文史料稱「大夏國」為「西夏」。將藏巴王朝視為朝代名稱並冠予方位,也就順理成章稱為「西藏」了。簡而言之,西藏的產生過程是︰地區名→朝代名→西藏,或者說︰藏→藏巴王朝→西藏。所以,「西藏」一詞直接對應的是「藏巴王朝」,而不是藏巴王朝的詞源「Gtsang」這個地區名稱。
中國藏學家陳慶英認為「西藏」一詞最早出現於清朝滿文奏章中,應該是滿文「西部藏」意思的漢譯。雖然如前所述,滿文檔案的「西藏」並非是第一次出現,但上述兩個來源相互並不矛盾,或者說具有互補性。因為滿清和西藏初次建立聯繫的時候,西藏還在藏巴王朝末期,達賴喇嘛的代表到盛京見滿清皇帝時,滿清皇帝的回禮中就有給藏巴汗的信件和禮物。這其實也反證了「西藏」是源於藏巴王朝的,因為除了藏巴王朝,實在找不到理由說明為何在明朝大臣或滿清皇帝的視野中竟然會出現「西藏」這個詞彙。正如漢族的稱呼源於漢朝,唐人的稱呼源於唐朝一樣,西藏這個稱呼也源於西藏歷史上的藏巴王朝。而達賴喇嘛領導的噶登頗章政權就是在推翻藏巴王朝後建立的。
另外,不論何時,「西藏」從來都沒有用來指稱「Gtsang」地方。同樣,不論何時,「西藏」一詞都能夠實現「民族和地域」的雙重指代功能︰西藏人=西藏民族,西藏語=西藏民族語言,西藏服裝=西藏民族服裝等等。此外,正如十七條協議的前言中多次出現「西藏民族」這個概念,表明共產黨也並不認為「西藏」只是一個地區的名稱。
如果說歷史上「西藏」的範圍曾有大有小,那只是根據藏民族建立的政權所控制地方之大小而隨之發生變動。
還有,西藏一詞並不是到國民黨時候才普遍使用,而是在滿清中後期就已經普遍使用。我記得乾隆皇帝立在拉薩的石碑中,就已經是「西藏」和「圖伯特」混用,而且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從那以後,滿清的資料中一般都以西藏稱呼之。在此之前,稱呼「西藏」的較少,但不是沒有,如西元1699年滿清將領岳升的奏章中就寫「臣查打箭爐各處地方,向系藏人霸佔。」等。而一直到七世達賴喇嘛為止,西藏政府的統治範圍是包括整個西藏三區的。
其他還可以舉出一些理由,但我覺得以上就足夠了。
三、我不反對使用「圖伯特」,但反對取代「西藏」。
我的一些朋友也不喜歡使用「西藏」這個概念,我都是建議他們使用圖伯特。因為這是從西元八世紀開始就有的稱呼,第一次是出現在西元八世紀回紇汗王(現維吾爾或廣義的突厥)的碑文,而且也與英文等直譯相配合。
但我反對一些人主張的用「圖伯特」取代「西藏」的觀點。這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是沒有意義。 因為,不論「圖伯特」或「西藏」,翻譯成藏文都是「bod」。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圖伯特」或「西藏」的內涵外延只能根據藏文「bod」來定義,這就足夠了。
而且,在中文史料中,「西藏」也使用了幾個世紀,難道在此期間中文史料中的「西藏」所指的竟然是只有幾十年歷史之共產黨的「西藏自治區」或是範圍更小的國民黨的「西藏地方」?抑或是藏文的Gtsang地方?近代而言,《十七條協議》有藏中兩種文本,「西藏」與對應的「bod」所指的難道是「西藏自治區」?或是國民黨的「西藏地方」?
再往後,聯合國曾透過有關西藏的決議,中文是聯合國的法定用語,決議中文版使用的是「西藏」這個詞彙。難道我們認為聯合國透過的有關西藏的決議所涵蓋的範圍只有「西藏自治區」或是「西藏地方」?而另一個問題是︰簽定十七條協議或聯合國透過決議時,「西藏自治區」還連個影子都沒有,而「西藏地方」不僅範圍比「西藏自治區」小將近一半,而且主張這個概念的國民黨已經被趕出了中國。
如上述,我並不反對使用「圖伯特」,正如滿清皇帝在拉薩的碑文中那樣,「圖伯特」和「西藏」可以並用,因為兩者都是外民族對「bod」的指稱,並不存在高低上下的涵義。也因此,我反對以「圖伯特」等來取代「西藏」或廢棄使用「西藏」。
另外,我反對西藏議會使用「圖博」的決議,認為「圖博」這個詞彙是一個沒有歷史根據或現實基礎的人造概念。中文史料上從未使用「圖博」這個詞彙,這是一個憑空人造,沒有人知道出處,也沒辦法望文生義,更沒有被任何辭典所收錄的新詞彙。
懸鉤子質問我:「我請您捫心自問,西藏一詞是為了博巴長遠的利益著想嗎?您一個人武斷地自認可以代表所有博巴,專斷地決定了所有博巴的國名,您如此作法,究竟獲得了誰的授權(mandate)?其民意基礎又何在?您對得起先人正名的努力與苦心嗎?未來的子子孫孫就該這樣永遠屈從,以中國人的意旨為意旨?」
對懸鉤子的質問和公開信,我發自內心地充滿感激,因為其中表現的是對西藏一片真情摯意的關懷。同樣,我是一個西藏人,我對自己的立場有明確的認知,這不會受在中國或在台灣或美國受教育所影響,我們的任何選擇都要考量歷史、現實以及西藏民族的長遠利益等不同層面。也因此,我才會強烈反對西藏議會有關使用「圖博」(注意,不是「圖伯特」),停止使用「西藏」的決議。當然,我提出反對意見不需要誰授權,因為這是我在行使言論自由。自然也談不上武斷,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權力和資格。正如我前面指出的那樣,流亡西藏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反對意見和理由。當時,支持和反對雙方之間進行過辯論,開過研討會,也曾分別寫辯駁文章等,這一切以後,西藏流亡政府和議會接受了我的意見,繼續使用「西藏」一詞,僅此而已。
台灣由於西藏流亡議會曾通過的決議而陰差陽錯地普遍使用「圖博」,這是一個錯誤造成的誤解。當然,現下有不少人將其視為台灣抵制中國本位主義的符號,如此則又另當別論了。
四、有關正名
懸鉤子的信中談到了正名問題,而且非常正確地指出︰「就如同目前圖伯特境內所出現的康定、久治、西寧這些地名所暗示的,外來統治者正忙著切斷被統治者的文化根源,其心昭昭。」
清人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中說︰「滅人之國,必先滅人之史,史亡則國亡。」 懸勾子上述切斷文化根源等,其實就是「滅史」的表現之一。
大部分被統治、被殖民的民族都只能面對這一切,就像台灣原住民在日據時代改日本姓名說日語,國民黨蔣家時代改漢姓說漢語一樣,很多被滿清國民共黨統治地區的藏人也被迫起漢姓漢名;不論滿清國民或共產,他們在佔領西藏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設立官府和建立學校,官府代表征服,學校則成為消滅自己的民族史、灌輸統治民族歷史和價值觀的同化(滅史後的結果)工具。其最終目的都是要消滅西藏民族。
「滅史」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讓其完全消失;另一種是改頭換面,留其殼,改變其內涵外延。而中共對「西藏」採取的恰恰是後者。如前所述,「西藏」得名於藏巴王朝,是一個西藏的朝代所衍生出來的概念,但中共卻極力避免提及或掩蓋這個事實和過程,而是取其與藏文「Gtsang」的聯繫,並且強化之、等同之,給人一種西藏的範圍僅限於「Gtsang」或所謂「前後藏」地區,以及史料中西藏的活動範圍僅限於「Gtsang」地方的印象,從而使其「分而治之」西藏的政策合理化等。
簡單地說,如果西藏人贊成棄用「西藏」,就等於承認中共對「西藏」的解釋;就等於承認中文史料中記載的「西藏」,以及十七條協議或聯合國決議等所有出現中文「西藏」詞彙者,其所指範圍僅限於西藏自治區或「Gtsang」地方。那怕僅僅是從功利的角度而言,這樣對西藏又有什麼好處?
綜上說述,「西藏」這個詞彙本身,並不是「兼具有占地野心與帝國主義的」的辭彙,也不是「帝國主義的中國所使用、縮限(說直接一點,就是矮化)的名詞」,相反,它實際上表現的是西藏歷史上的一個朝代,一個國家,一個獨立的政權。也因此,不使用它,承認中共對此的定義,漠視或放棄它原來所具有的歷史涵義等,那才是真正的「以中國人的意旨為意旨」。
五、其他的一些問題
信中談到「這樣的說法不正是您說的『博巴不追求基本人權,只要生存』的論調?」
我不知道我的原話是否表達清楚。我平常所說的是「西藏人追求的還不是人權,人權對西藏人而言是奢侈品;西藏人尋求的是民族的生存。」我還會強調︰「人權是活的好不好的問題,而對我們西藏民族而言,面臨的問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如果這個論調有什麼問題,那是我的責任。
公開信中還談到:「當時的格桑澤仁大概不會想到時隔不及百年,博巴後人就已經決定自廢武功,為了遷就中國,連族名都可以不必堅持了」。
這個世界的絕大部分民族都有自稱和他稱,這兩者並不一定是一致的。如中文的「土族」,藏語稱為「霍爾」,蒙古人稱其為「白韃靼」,他們自稱則是「蒙古爾」。我想,不會有人要求中國人、西藏人或蒙古人放棄原有的他稱,改而統稱「蒙古爾」吧!堅持族名指的是自稱的堅持。至於他稱,除非有侮蔑、歧視或貶損之涵義存在,否則,看不出有提出改變的必要。正如我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西藏」並不具有歧視或貶損的意思,和圖伯特、唐古特、菩提亞等一樣,都是外人對自稱「bod」之民族的他稱。
至於格桑澤仁等人,他們對西藏人而言,就像中國的汪精衛,肯定不配稱為我們的前人。他們都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分,承認國民黨對「西藏地方」的定義,因此,即使如願改名,「西藏地方」的實質不會有任何改變。我按公開信的網址看了該文,當時的西藏獨立地位可謂是舉世公認,但這些活寶卻在中國議會提出在西藏修建鐵路的議案,格桑澤仁就詢問「康青、青藏兩公路之保養及利用」的問題。就像改族名一樣,他們不過是在根本不是問題的地方找問題,卻迴避或不敢正視真正的問題──西藏民族世居之地就叫「西藏」。
如此等等,我就不一一解釋了。最後,不論我們的立場或觀點是否相同,我發自內心地充滿感激,因為懸鉤子的公開信中表現的是對西藏一片真情摯意的關懷。感恩關心西藏的諸位朋友。謝謝。
達瓦敬俱2011/05/12
附錄:
《明實錄》
萬曆三年四月甲戍(1575年5月15日)
俺答子賓兔,役屬作兒革、白利等諸番。隨令寄信松潘番、漢,以迎佛蓋寺為名,屢傳衅息。四川撫臣曾省吾、按臣郭莊以聞。謂:「宜速行陝西總督諭令順義王俺答,嚴戢賓兔,無得垂涎邊境,自敗盟好。」於是,兵科給書中蔡汝賢奏言:「賓兔蠶食諸番,撤我藩籬,逆志固已萌矣。議者不察,猶欲傳諭俺答,鈐制賓兔。夫奄奄病酋,墓木已拱,安能繫諸酋之手足耶?且賓兔前搶西寧,已行戒諭,曾莫之忌,可見於前事矣。乞敕該部亟咨該鎮,勘破虜情,整搠邊備,或先事以伐其謀,或遣諜以携其黨,或增兵以扼其隘,或相機以挫其鋒,令犯順者創,脅從者解,狂虜聞之,少知斂戢爾。且虜自稱貢以來,所要我者屢變,索鍋而與之鍋,求市而與之市,增馬而與之增,將來邊計安知底止!乃若巴蜀之衅,又自焚修之說啟也。蓋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彼黠虜豈真有從善之念哉!其挾詐用術,遠交近攻,不獨賓兔為然明矣。惟天語叮嚀當事諸臣毋蹈往轍,克勵新圖,無苟取一時之安,重貽他日之悔。」章下兵部。
梁本卷三七‧頁二下-三下 館本卷三七‧頁二下-三上
Posted by rosaceae at 12:08│Comments(0)
│必也正名乎
※このブログではブログの持ち主が承認した後、コメントが反映される設定です。